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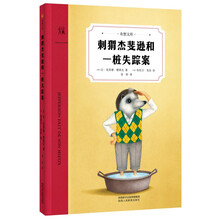
马修?卡思伯特驾着栗毛牝马前往八英里外的布赖特河。沿路是一排排舒适的农舍,冷杉树散发着树脂香气,野杏树不时在山谷间露出薄膜般的花瓣。苹果园和青草地隐没在地平线紫白色的迷雾里,空气弥漫着清甜的芬芳。
“鸟儿轻轻唱,歌唱这最美丽的夏天。”一路上马修自得其乐,除非遇到不得不向过路妇女频频点头的场合——爱德华王子岛风俗如此,你应该向路上碰到的所有人点头致意。
马修害怕女性,除了玛丽拉和雷切尔太太。他总是别扭地感到女人会背地里笑话他。这种担心可不是没来由的,他相貌古怪,姿态笨拙,佝偻的肩膀上垂着铁灰色的乱发,从二十岁起就蓄着满脸柔软的褐色大胡子。事实上,他的二十岁跟六十岁长得没什么两样,除了须发变得更灰白。
来到布赖特河,马修没有看到火车。他猜是来早了,就在布赖特河小旅馆的院子里勒马停车,走进火车站。长长的月台荒凉至极,有个形只影单的小姑娘,坐在站尾一溜儿木瓦片上。马修几乎没留意到她是个女孩,便略略侧身快步走过,甚至没有看她一眼。如果他多看一眼,就会发现她紧张僵硬的姿态和满怀期待的神情。她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只好全神贯注地静坐等候。
马修遇上火车站长,他正要给票务处落锁,准备回家吃晚饭。马修问他五点三十分的车是不是就要到了。
“五点三十分的车都离站半小时了,”站长乐呵呵地回答,“不过有位乘客给你留了个小女孩。她正在外头瓦片堆上坐着呢。我请她进女宾室休息,她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她喜欢待在外头,‘外面更有想象的空间’。嘿,我说她够古怪的。”
“我要找的不是女孩,”马修讷讷地说,“我来找一个男孩,他应该在这里等我。是亚历山大?斯宾塞女士从新斯科舍领过来的。”
火车站长打了个呼哨。“我猜肯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他说,“斯宾塞女士下车把那女孩带到我面前,说你们兄妹从孤儿院领养了她,一会儿你就过来接人。我知道的就这些,这可没藏着别的孤儿喽。”
“我可闹不懂了。”马修无助地说,打心底盼望玛丽拉能在这里扭转乾坤。
“你最好问问那女孩,”站长不在意地说,“我敢说她肯定很清楚——小姑娘嘴巴伶俐着呢,可能孤儿院没有你想要的男孩了吧。”
他肚子饿得咕咕叫,说完就快活地回家吃饭了。倒霉的马修只好独自处理这件事,对他来说,这无疑比独闯狮穴更为可怕——去陌生的小孤女面前,责问她为什么不是男孩。当马修掉头往月台走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灵魂发出了一声呻吟。
自打马修经过身旁,她一直注视着他。当时马修并没有看她,对小姑娘的容貌也就没有留下印象。正如大家所见:这是一个大约十一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紧小难看的灰黄色绒衣,头上戴着褪了色的棕色水手帽,帽子下压着浓密的红头发,两条粗粗的麻花辫一直垂到背上。她有一张小脸蛋,瘦瘦白白,点缀着许多雀斑,嘴巴和眼睛都很大,瞳仁平时是灰色的,在光线照耀下或者情绪波动时则变成绿色。
而敏锐的目光则会发现,她有着尖细的下巴,面部轮廓分明,一双大眼睛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嘴型甜美而且表情丰富,额头宽广饱满。总之,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让马修羞惧不安的这位小孤女,体内栖息着不安分的灵魂。
不管怎样,马修总算摆脱了向女性搭话的煎熬。看见马修靠近,孩子主动站起来,一只细瘦的棕色小手抓起破旧的毛毡小提包,另一只手伸向他,“我猜你就是绿山墙农舍的马修?卡思伯特先生吧,”她的嗓音清晰甜美,“非常高兴见到你。刚才我还想,可能有事把你绊住了,如果你今天晚上不出现,我就沿着铁轨走到那边拐角,爬到那棵巨大的野樱桃树上睡觉。我一点都不感到害怕,月光会把大樱桃树和它的花朵儿都照得白莹莹的,感觉就像睡在大理石宫殿一样!而且我相信,即使你今天晚上来不了,明天也一定会来接我的。”
马修笨拙地握住那只细瘦的小手,暗自作了决定。他无法对这个扑闪着大眼睛的小姑娘说出真相,但他可以把她带回家,让玛丽拉去做这件事。无论中间出了什么差错,他不能把这个小女孩扔在布赖特河不管,棘手的问题不妨留到绿山墙农舍解决。
“抱歉我迟到了,”他羞涩地说,“来吧,马车停在院子里。我帮你提着包。”
“没关系,我拿得动。”孩子笑盈盈地回答。“虽然我把全部家当都装进去了,可是真的一点都不沉。拿这个包需要特别的小技巧,不然提手就会掉出来——还是让我自己拿着吧,它已经太旧了。在樱桃树上睡一觉尽管也不错,但是你能来我实在太高兴了。我们要走好一会儿,对吗?斯宾塞太太说有八英里远。我一直盼着可以坐马车呢。噢,我将加入你们的家庭,和你们一起生活,这实在太美妙了!我还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家庭生活呢。孤儿院太可恨了,我在里面待了四个月,可算是受够了。我猜你没去过孤儿院吧,你没法想象那里的生活有多恶劣。斯宾塞太太说我总是滔滔不绝,我可不是故意的。人们总是不知不觉就爱犯错,不是吗?孤儿院有很多好人,但是那种地方缺乏想象的空间。我时常想象孤儿们的身世,可有意思了。比如邻桌的女孩,我想象着她其实是一位绶带伯爵的女儿,坏心眼的奶妈把她从父母身边偷走了,可惜奶妈来不及说出真相就咽了气,所以她才流落到孤儿院来。我晚上一躺在床上,就会不停地东想西想,可是白天就没有工夫乱想啦。我猜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长得这么瘦。我瘦得很吓人,是吗?我身上都是骨头,捏不到肉。我常常想象自己相貌美丽,身材丰满,胳膊肘上能挤出小肉窝才好呢。”
说到这里,马修的小伙伴安静了下来,一半是因为气短,另一半是因为马车已经出现在眼前。直到驶离这个村落,她都没有再说话。马车沿着陡峭的山丘向下行驶,马路挖得很深,两旁堆起的土坝比人还高,坝上栽种着一排排繁花满枝的野樱桃树和纤细修长的白桦。
野樱桃树的枝条抵着马车,孩子伸出小手,“啪”地揪下一根来。
“这多漂亮啊,不是吗?”她说,“看这坝上白花儿绽放的大树,你想到什么了?”
“呃,我不知道。”马修说。
“当然是披着雪纺婚纱的美丽新娘了。虽然我没见过,不过一定就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想象成新娘子。我长得太丑了,不会有人娶我的,除非是外国的传教士。我想外国传教士应该不会很挑剔吧。不过,我一直盼望着哪天能穿上白纱洋装,这是我最幸福的理想了。我喜欢漂亮的衣服,可是从来没有穿过可爱的洋装。不过,我们当然要对未来抱有希望,你说不是吗?我可以幻想自己穿着落地长裙,举止优雅高贵。今天早上,我就穿着这身可怕的绒布裙离开孤儿院,心里可难过了。我只有这身衣服,孤儿院的孩子只能穿穿绒布裙子。去年冬天霍普敦的商人捐赠孤儿院三百码绒布做衣服。传说那些绒布是卖不出去才捐赠的,不过我宁愿相信他是出于好意,你也这么想吧?在火车上,我觉得大家都用同情的眼光盯着我看。可我不在乎,自顾自地幻想身上穿着最漂亮的淡蓝色丝绸长裙,头上戴着用鲜花和羽毛装饰的大帽子,手上戴着金表、儿童手套,脚上蹬着小皮靴——既然是幻想,不妨尽善尽美。想着想着我就开心起来,一直快快活活地来到岛上。坐船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晕,斯宾塞太太说她光顾着操心我,害怕我蹿来蹿去会掉进海里,压根儿就没工夫晕船。她有晕船的毛病,如果这对她有帮助,我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啦。我真想把船里船外都看个遍呀!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看到。这个岛就像一座花海,到处都是樱桃树,树上开着满满的花朵。一看到这个岛,我就爱上了它,能住在这里是多么的幸福啊!以前我就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我常常幻想能住在这里,没想到竟然梦想成真,感觉实在太美妙了!那里的路真奇怪,火车一开,红色的路就刷刷地从眼前闪过。我问斯宾塞太太,路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呢?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求我不要再问了。她说我已经问了她一千个问题了,我猜这倒是没错儿。可是,不问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你说,到底为什么路是红色的呢?”
“这我也不知道啊。”马修说。
“噢,以后我要想办法弄明白这个问题。思考那些未知的事情难道不是很美妙的吗?寻找答案让我觉得世界充满了乐趣,活着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如果我们什么事都知道,生活就少了许多乐趣,可以想象的空间就没有了。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大家都抱怨我太啰唆。你是不是想我少说几句?如果你不想听,我会努力闭上嘴,虽然这很困难。”
马修惊奇地发现,小女孩的絮叨还挺有意思的。像大多数沉默寡言的人一样,他喜欢听健谈的人说话,只要他们能自顾自地说下去,别要求他参与谈话。他可从来没想过和女孩分享她的小世界。跟女人相处就够头痛的了,小女孩则更难忍受。他最痛恨阿冯利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女孩,老是从他身边鬼鬼祟祟地溜过,却同时拿眼偷觑着他,好像她们一出声就会被他活吞了一样。但这个满脸雀斑的小鬼头和她们完全不一样,尽管他觉得自己迟钝的脑筋很难追上她飞快跳跃的思维,她唠唠叨叨的话却让他挺高兴的。因此他像往常一样腼腆地说:
“你想说就说吧,我不介意。”
……
——翻译家李文俊
作为一部穿越了时空,在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熠熠生辉的作品,蒙哥马利的“安妮”系列为世人塑造了一个叫安妮的女孩的形象。这个形象,始终占据世界文学长廊的一方天地,在那里安静却又生动无比地向我们微笑着,吸引我们驻足,无法舍她而去。
——作家曹文轩
安妮是继不朽的艾丽丝之后*为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