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1869年问世,这家犹太人创办的企业一直以信誉为名。细究起来,公司最疯狂的一次冒险发生在1929年前后,那一次的严重失误险些使之破产,成为美国金融界最大的输家和笑柄。
此后的高盛幡然醒悟,一步步走上正路,在恶意并购大行其道的20世纪70年代,它毅然站到所有同行的对立面,声称要以自己的专业能力“保护受害者”,公然与恃强凌弱的投行进行搏斗,最终借此跻身世界顶级投行之列,从而完成从一个草根票据公司到“投行贵族”的华丽转身。
与大多华尔街投行不同,高盛一直到1999年才挂牌上市。严格来讲,它并不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公司。为吸引人才,高盛内部推行私人合伙制。通常情况下,最优秀的一两位合伙人被任命为管理者、联合主席,他们只对合伙人负责,拥有极大的行动自主权,因此受监管程度较低,向公众披露信息的义务也少得多。
这种制度设计最大程度激发了个人能力,一度成为高盛的企业文化。公司极为珍视合伙人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合伙人的利益,为每一位合伙人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酬,由此聚拢了一大批顶尖金融人才。
1994年,公司的股本回报率达到60%以上,当年年底,每一位合伙人从公司分到不少于400万美元的利润。但还是有一大批合伙人离开了高盛,这种事情在过去不仅从未发生,而且难以想象。
离开的合伙人任期短并且年轻,他们主动放弃唾手可得的利润,似乎是提前意识到了危机。
在1992年离开的领导者罗伯特·鲁宾看来,巨额利润已经把高盛中潜在的危险掩盖了,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你骄傲、利己、自大和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你就将失败。”话是对他的同事和下属说的,但鲁宾没能改变这种局面。1992年,他把这个任务交到接任者斯蒂芬·弗里德曼手中,自己给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当幕僚去了。
弗里德曼是一个意识超前的指挥家,他对发生在眼皮下的事情给予高度关注。他甚至在年底的庆功会上花费大量时间提醒其他合伙人,警惕即将到来的危险。
弗里德曼看得很清楚,被人诟病的是高盛的超级分红制度——如果交易商在交易中获得成功,年终可获得数百万美元;如果没有取得成功,即便损失惨重,仍旧可以拿到薪水。这种机制的隐患在于,鼓励交易员疯狂冒险,不惜代价获取利益。大批合伙人的离开是因为对这种交易行为感到不满,并质疑它对于整个公司的作用。
针对公司内部的自得情绪,弗里德曼警告说:树再长也是不能冲破天空的。他希望借助循序渐进的改革来改变这种状况。
不幸的是,事态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公司盈利能力惊人、骄傲情绪四处蔓延,人们在分红面前变得狂热、焦躁,没有谁认为自己有错。不久,自信演变成自大。这恰恰为即将到来的萧条埋下了罪孽深重的种子。
危机择日而发。1994年的第一个月,高盛的经营情况比往常更加良好。这个月,公司创下3.75亿美元的盈利记录,是过去一年月平均盈利的1.5倍。公司上下进一步变得狂妄,乃至奢华。
媒体披露说,“他们包租飞机,购买伦敦带雨棚的公寓、西部的农场和私人酒窖,甚至还有人买了私人直升机”。要知道,这些事情几个月前根本没人敢想。与此同时,管理层开始分化,有人开始考虑上市,尽管在少数人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举动。
或许人们更愿意通过地理扩张来增加影响力。
1994年,高盛已经是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的综合公司,业务宽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它经营咖啡和木材生意,承购债券和股票,安排兼并,以自由资本向成长中的企业投资。年初,公司内部流传着一个扩张方案:在全球增设分公司,招聘更多员工,扩大公司规模。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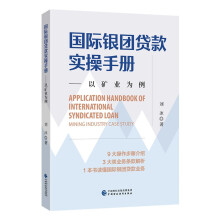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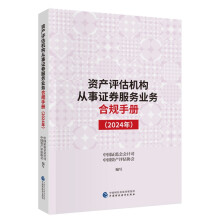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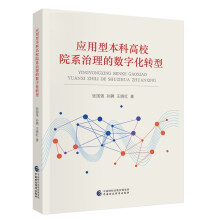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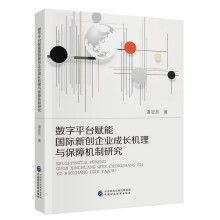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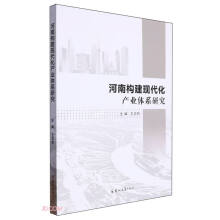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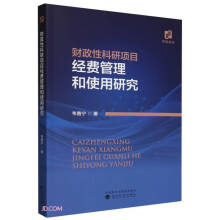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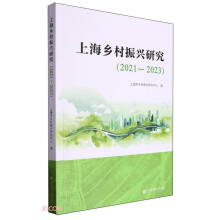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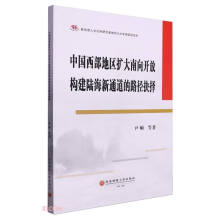
与其他同行相比,高盛是中国市场中的姗姗迟来者。但是,高盛进人中国市场后,迅速创造了令国内外同行羡慕不已的众多“第一”,甚至是“唯一”。
《21世纪经济报道》
事实证明,高盛曲线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策略非常高明,不仅取得了一家中国投行的管理和财务控制权,而且一举奠定了高盛在中国境内大型投行项目的主导地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平安保险、中兴通讯、交通银行、中国石油(后续股票发售)、中国银行、中海油海外上市等具有全球影响的皇冠级lPO融资项目悉数被高盛收入囊中。
《中国企业家》
高盛“对中国业务的参与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却在投资银行的合资一事上一直处于谨慎甚至保守的状态。无论国企重组、金融改革还是制造业,高盛在中国的策略都是“猎大象”。
《中国青年报》
和许多金融巨头一样,高盛进入中国所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获得中国企业的控制权,然而,由于中国许多行业和企业的股权都设定了最高的转让权限。因此,尽管外资投行机构手握巨资重金,最终还是英雄气短。然而,这一看上去似乎无法跨越的政策难题在高盛手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悄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