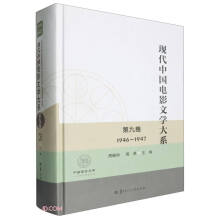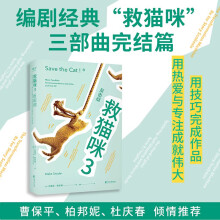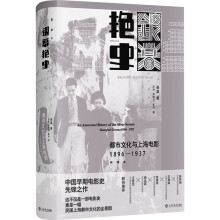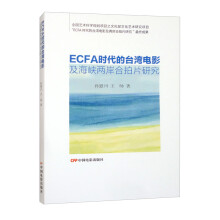《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
1.主题书写
台湾“反共片”的主题书写具有一成不变的套路。不管是50年代流行的“匪谍自首”、“共党阴险”剧情,60年代流行的“投奔自由”故事,还是70年代对“大陆沦陷苦难”的想象,1980年代“共党阴谋”和“大陆崩溃”交替呈现的宣传模式,反共电影总能在简陋肤浅的故事中,贴上“反共复国”的政治标签,极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并对当局的政策信息和意识形态观念进行注解。每一部“反共片”就像一篇急就章的政宣论文,剧情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每一处道具,都在极力为“中心论点”提供“论据”,以顺利导向最后的“反共”结论。这种急功近利的艺术心态,使“反共片”的主题书写往往显得异常生硬俗套。即使有再新的形式包装,类型电影的外观仍然是“反共”政策的内核,一以贯之的情节推进模式总能让观众一眼望穿。从开端到结局,一切似乎已各就各位、早有定论,观众只需要在影片的末尾再次印证已有的观影经验就行了。
1970年拍摄的《歌声魅影》,被改造成“推理间谍文艺歌唱片”,但它的情节推进路线、角色命运结局和传统的“反共”政宣片几乎完全雷同。在这些影片的情节设计中,“恶贯满盈”的共产党员往往受人利用,在组织的“教唆指使”下进行破坏行动,在结尾总能“良心发现、幡然悔悟”,要么被国民党的“慈爱关怀”感动,要么被当局“自由宽大”的政策感化,要么在爱情中找到栖身台湾的理由,总之,他们的“回心转意”将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配合“保密防谍”宣传的社教片中,“觉悟投诚”的共产党员因被“组织”发现,面临被杀人灭口的危险。编导往往在大肆渲染共产党“赶尽杀绝、惨绝人寰”后,让历经险境的主人公在结局实现命运逆转。
60年代前的“反共片”以“匪徒自首回归”的圆满结局居多,《梅岗春回》《罂粟花》《歧路》等片均皆大欢喜,显见国民党“反共复国”的乐观心态。之后的影片多以悲剧作结,《奔》《夜尽天明》《雪花片片》等影片中,被策反成功的“匪党”多命丧黄泉,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也显示了国民党在“反共”目标上的悲观心态。不管是“被杀成仁”还是成为“反共义士”,“反共片”中的“共匪分子”形象都已成为台湾当局意识形态的化身,他们的命运在正衬或反衬的情节思路中,不断印证“反共主义”的合理性。
在《血战大二胆》《古宁头大战》《八二三炮战》《狭谷军魂》等战争反共片中,不管历史事实如何,在充分渲染了对方的“狡诈凶狠”之后,国民党军队总能出奇制胜,将敌人推向必然覆灭的固定结局。这样千篇一律的主题程式,不仅为国民党政权提供了阿Q式的心理安慰,也为岛内民众提供了“反攻有望”的梦幻场景。李嘉导演的《狭谷军魂》(《黑夜到天明》,1963)竟然假想了一幅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的理想场景:武装特务空降至某峡谷,在所谓“游击女战士”的配合下,从黑夜固守到天明,等“反攻大军”赶到,终于完成使命。《魔窟杀子报》(1959)的结尾,同样是国民党“游击队突袭成功”,“匪徒”死于非命的大圆满结局。在台湾“反攻大陆”屡败屡战的60年代,这些虚假辉煌的景观是如何获得观众认同的?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一成不变的“反共复国”主题宣传,使国民党在画饼充饥中弥补了些许失落忧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