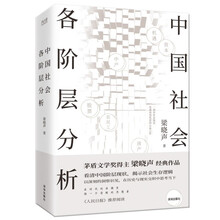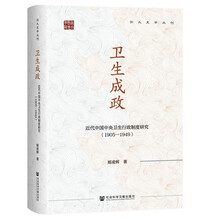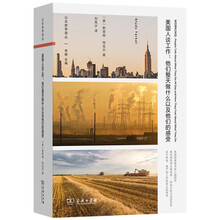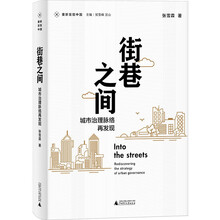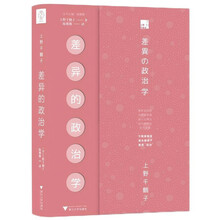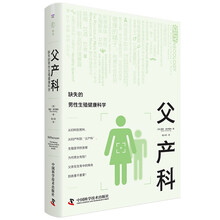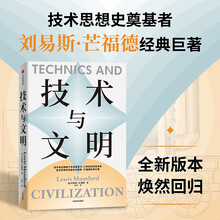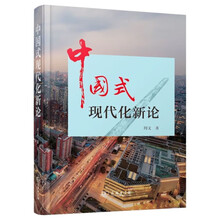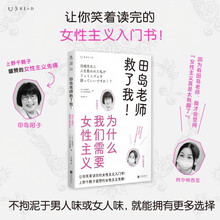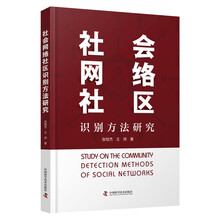在社会学者看来,情绪研究的重点不仅在于个体的情绪体验和表达,更在于那些决定了我们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基础、为何种原因、以何种表达模式、体验到何种情绪的社会脉络。在展现了高中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情绪状态及其变化历程之后,本章的目的在于超越个体心理现象的范畴,把情绪视为一种个体间现象,在人际关系与变革脉络中探寻教师情绪的形成原因。
通过对田野资料的分析,本研究归纳了影响教师情绪的两大类互为补充的因素。一类是课程实施中的“教师-他人”互动,这类因素可以通过哈格里夫斯等人界定的“情绪地理”得以解释,即由教师与他人之间的人际互动形成的社会空间模式激发或影响着教师情绪。具体而言,根据导致这种社会空间模式之因素的性质,情绪地理可分为政治、专业、道德、物理和社会文化五个维度。另一类是课程实施中的“改革-情境”关系,这类因素可以通过本研究所界定的“情绪困境”得以解释,即由改革及其所处情境之间的张力结构造成的困境引出或干扰着教师的情绪状态。根据导致这种困境之因素的性质,情绪困境可分为文化、制度、专业和资源四个维度。概括起来,情绪地理关注的是影响教师情绪的人性化的个人因素,情绪困境处理的则是影响教师情绪的非人性化情境因素。
尽管做出上述分类,我们仍然需要注意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情绪地理与情绪困境之间会发生互动。在课程实施中,“教师-他人”互动总是在“改革-情境”张力结构中进行的。由于困境会对所有参与者造成情绪干扰,这成为“教师-他人”互动中预先存在的情绪背景。同时,从人际互动入手解决教师的情绪问题也是缓解困境给教师带来情绪紧张的途径之一。例如,文中提到的那位不负责任的教师培训者既会使教师情绪受到政治地理学的影响,又会导致教师在实施中面临更加严峻的专业困境。另一方面,情绪地理与情绪困境内部各种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正如哈格里夫斯所说,仅在一个维度上增加教师与其互动同伴的接近程度并不一定能够建立情绪理解,而他们在一个维度上的距离可能也会对他们在其他维度上的接近造成威胁。 例如,教材编写者、专家与教师的地位差异导致他们对教师专业能力的质疑,这使他们无法共同探讨课程实施中的一些专业问题。在情绪困境中,各个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存在。例如,教师在课程实施中面临的资源困境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关于高中课程改革“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想法,从而加剧了改革与其情境之间的文化困境。
概言之,对情绪地理和情绪困境中的分析表明,把情绪理解为社会文化建构的观点是完全可行的,它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生成性(emergent)产物”。从课程实施中的人际互动和“改革-情境”关系出发审视情绪,有利于我们发现教师情绪负载的社会信息。在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遵循赞比拉斯的建议,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在群体间水平上分析特定情境中的社会文化规范与教师情绪之间的关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