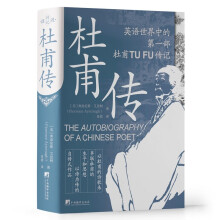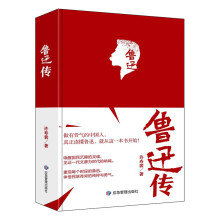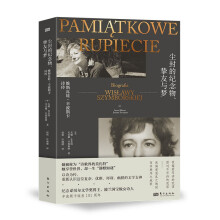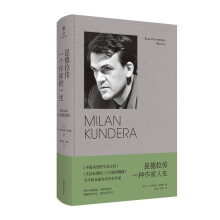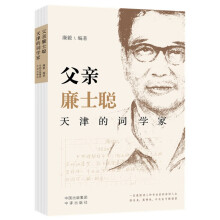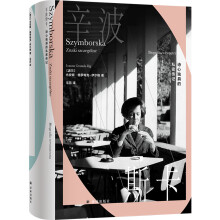函可讲法成功的关键是主讲禅宗。由于明朝初年重视佛教的传播,各佛教宗派如禅宗、净土、天台、贤首、律宗等竞相发展,至明中叶后,天台、贤首等诸宗渐渐衰息,而禅宗颇为盛行。禅宗不立文字,专指心源。禅宗创始人慧能(638-713)大师,认为佛既不在彼岸,也不在此岸,就在人的心中。心中之佛,才是真佛,才会为人所用。慧能进而认为,修行者想成佛,不必选择外求的路向,在“心”上下功夫即可。慧能还认为,众生都有“佛性”,只要领悟此点,人人都可以成佛,特别是不用累世修行,也不需要布施大量财物,即可“顿悟成佛”。如何能“顿悟”,关键要做好“禅定”即修行者“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
慧能大师以“见性成佛”为宗旨,提倡不立文字,弘扬“顿悟”禅宗教义,为禅宗制定了理论框架和思想基础。他身后多位禅宗大师弘扬不辍。到憨山禅师(1546—1623)时尤大力弘扬禅宗,力倡“儒佛合一”。此观点大大拉近了僧俗之间的距离,更加增强了岭南文士对佛教的兴趣。聪明过人的函可经多年研修,对禅宗宗旨深谙娴熟,笃信不疑,完全融入自己的讲法中。由于禅宗颇具人性化的教旨,特别是讲到能否成佛,强调众生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此教旨不仅适应精英层的口味,也适应社会下层的诉求,所以为函可开法成功奠定了基础性前提。 然而,任何宗教派别的经文都是艰涩、枯燥的。禅宗经文也不例外。那么,函可演讲为什么能吸引僧众呢?细品《语录》内容,可发现函可开法时,有精妙的讲经艺术,即不是背诵枯燥的经文,而是用平实、通俗的语言,讲解他所要讲的经文。特别是不就经文注经文,而是针对僧众存在的“活思想”,将自己摆进去,有理有据地娓娓道来。《语录》卷五《普说》篇颇有代表性。比如,针对一些出家人担心“作佛不成,反被他人耻笑”而“虑得虑失”“屡进屡退”的现象,函可打个比喻进行规劝:“譬如人家生个孩子决定与他乳吃,难道怕人耻笑道者个才出胞胎底孩子,知他后来长得成长不成,便索性不与他乳吃不成?又如学堂里学生,决定教他读书。难道怕人耻笑道者几个学生知他后来中得中不得,便索性不教他不成?”针对一些出家人急于成佛的心态,函可比喻说:“世间百工技艺也无有一日二日学得底,何况作佛,最尊最大一件事。譬如种稻最易,见功也须春耕夏耘而后秋收有望。宁有今日下种明日收割之理?”针对两种现象,函可的结论是:“汝但辨一片决定心,长久心,切不得怕人耻笑,不得要求速效”,“诸兄弟只恁作去,不愁不成”。
函可讲法时不是一言堂,常伴有互动环节。如《普说》篇记载,函可说法中间,李居士插话问和尚:“历来士大夫学道多不得力,病在何处?”对此问,函可滔滔不绝回答了好多话,道出许多病因,其中两点说得非常恳切:一是“要学此道必须发个狠毒,将无始来一点习气,千难割万难割处,痛下一刀,如破竹头一节,节节皆破,一切缠缚不得”。另一影响士大夫学道的原因,是将儒、佛对立起来,即“真儒不必为佛,真佛不必为儒”。针对此函可明确主张:“但为真儒,即为真佛。必为真佛,始为真儒。文章、风节、学问、经济,无不在此”,“倘其半信半疑欲前且却,则并无病痛之可指,至如阴窃先哲之绪余,假张学道之旗帜,招罗少俊私立朋党,以致荆棘丛生,戈矛互起,国家之败蔑不由之是,又无药可疗,无方可治”。函可开法互动环节,效果甚好,李居士听后思想包袱解开了,“不觉唏嘘涕下,命笔纪之。以为士大夫学道者鉴”。
函可开法过程中,又一可贵之处不是空疏说儒谈禅,而是在说教之外身体力行,为僧众做言行表率。函可阐释儒学核心“仁”时,调子很高,认为“仁者人也,非人外别有能谓仁”,“皇天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何止六经皆仁注脚,三藏十二部亦仁注脚也。何也?非此则断断不可谓人,非此则断断无别有可以为人之道”。函可将学仁做好人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观,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所以,开法时向僧众信誓旦旦地说:“罪秃之心不过求所以为人,庶几无愧吾亲,无愧于吾君,即无愧于孔孟,即无愧于佛祖。”本来,是为僧众讲佛经,应大讲佛教教义、戒律、经典等,而函可常常把话锋转到儒学上,而且再三强调不学儒就难学佛,不“欲仁”就难“为人”。一般意义上说,调子如此之高,内容又如此空疏,很难让受众信服,很难不使听者厌烦。可是结果恰恰相反,函可讲佛受到极大欢迎,“四辈皆倾”,究其原因这同函可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关系甚大。一年,盛京城从春天至夏季久旱不雨,城市外发生瘟疫,患者头痛腹胀、忽冷忽热、上吐下泻,几乎每天都有死于瘟疫者被送至城外掩埋,由此城中百姓惊恐万状,人们不敢出门,搞得大街小巷一片萧条。函可和尚见此情景,情急之下,大爱之心油然而生,他不辞辛苦,带领僧人奔赴盛京郊外东山嘴,采集马齿、霍香草等中草药材,经过加工煎制后,挨门挨户施送。有些患者持怀疑态度,函可等托言“观世音菩萨送来的救命草”,耐心劝人饮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