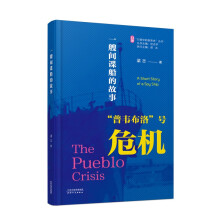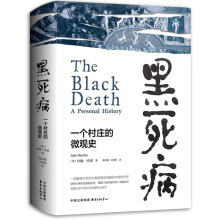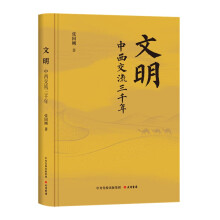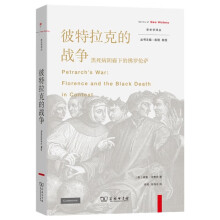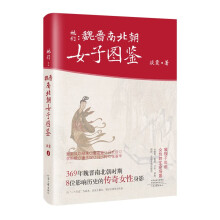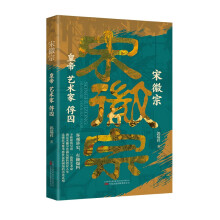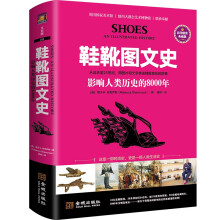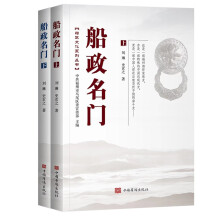第一章隐藏的“胎记”
在星光灿烂、浩瀚无边的宇宙中,有一颗蓝色的星球,它的名字叫地球。这是人类在穿过漫长幽深的黑暗岁月之后发出的由衷感叹。地球所散发的浅蓝色的绚丽光彩,其实是人类理性之光烛照的结果。否则,这个昼夜交替的星球就仍然还是黑暗的。
华夏文明的始祖神燧人氏,后来也叫炎帝,就是在漫长黑暗中孕育诞生的。这位始祖神之所以叫燧人氏,就是因她发明了人工取火这一夺天工之造化的神技,为我们先民驱散了黑暗,带来了光明,而被后世尊为“三皇”之首。炎帝也就是太阳神、火神的合体,也称“火祖”。高阳氏、高辛氏、祝融,都是这位“火祖”的子孙。华夏先民遵循的文化编码规则中,凡读“燧”音的汉字,无不与黑暗有关。“燧”表示取火工具,现代指燧石,在先秦时期则指钻燧取火。“燧”的意思是在木块上钻洞取火,也就是驱散黑暗;“隧”就是开掘黑暗而幽深的隧洞;“邃”指空间或时间的幽深黑暗,如同在幽深黑暗的隧洞中一样;“遂”表示完成,也就是从黑暗的隧道中走出来了。没有对黑暗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也就不会有燧人氏或炎帝,以及关于他们的诸多传说。华夏文明史,也就是一部华夏子民钻燧取火、走向光明的历程。这也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史。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久远传说,历久弥新,是对华夏文明历程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种隐喻和暗示。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阳光普照的隧洞之外,站立在人类一万年来文明成果堆砌的塔尖之上。
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行吟于南方的江汉平原,在《天问》开头连发27问,置疑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华夏文明的传世神话反复表现的其实就是一个母题:我们从哪里来。从某种程度而言,屈原对这个世界的置疑,也是对人类起源孜孜不倦的探索。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困扰屈原的无数问题已经成为科学常识,不再晦涩玄奥了。我们先民视为神圣的,现在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变得再平常不过了。也许,女娲用泥造人的神话传说,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这位始祖神在每个华夏子民的身上都留下了某种记号,也就是只有母亲才能辨认的“胎记”。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确都有“胎记”,只不过这个“胎记”的创造者并非女娲,而是地球这位造物主。这个“胎记”,就隐藏在我们每个生命个体的内部,并且无处不在。
如果说地球是宇宙的产物,那么人类则是地球的产物。人类拥有的206块骨头、640块肌肉、数十亿细胞的人体,都是地球的创造物。现代科学研究成果显示,在我们的体内,记载着恒星的诞生、天体的运行,甚至时间本身的起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与过去的陨石降落、大地震、海啸和大规模火山喷发等灾难有关。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每个生命个体的身体就像一张蓝图,记录着地球上所有生命从最初的单细胞生物到恐龙,一直到现代人类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中找到痕迹。
与此同时,科学的进步也在不断颠覆我们的传统认知。我们过去一直深信不疑的观点,被一次次反复证明是错误的。华夏子民从哪里来?谁是我们最早的祖先?几千年来的答案是:所有华夏子民都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可是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我们来自遥远的非洲。东亚大陆并不是我们的故乡,黄河流域也并非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我们只是东亚大陆的移民,并且是后期移民。
非洲是世界版图上的心脏。非洲的全称是阿非利加洲,意思是“阳光灼热的地方”。在这个光与热的王国,有着全世界最为神秘广阔的热带雨林,最长的河流,最大的沙漠,以及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密布的河流与湖泊。可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非洲更能使人类油然而生敬畏之情的了。在这片原始而古老、神秘而狂野的大陆上,生命的奇迹与壮美无处不在。人类就是从这片阳光灼热的地方走向世界各地的。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最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在此之前,达尔文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在完成漫长的环球旅行后,提出了他的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1859年,达尔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各种生物归根结底都来自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类型;进化导致物种的分化,生物不再被认为是一大堆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物种;每个细胞、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演变历史,都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它们目前的状态是它们本身进化演变的结果;生物不仅有一个复杂的纵深层次,它还具有个体发育历史和种系进化历史,有一个极广阔的历史横幅。基于这个观点,达尔文推测,人类并不是由一个全能的神所创造的,而是由猿猴慢慢演化而成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已经成为生命科学中不朽的基本思想,为科学家探究人类的起源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中进一步推测,人类的早期祖先曾经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别的地方。
自达尔文提出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以来,由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人类的摇篮最初曾一度摇摆于非洲、南亚、中亚、北亚以及欧洲之间。但这种情况在上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近一百年来,科学工作者工作者在非洲找到了大量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上世纪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更是惊喜连连,并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不断刷新我们对人类起源的认知。人类早期阶段的演化图景开始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阳光灼热的非洲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摇篮,很显然与其严苛而独特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其实,真正为“人类非洲单独起源说”提供最有力支撑的,还是分子生物学。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分子生物学的出现,使人类对生物体的认知逐渐深入到了微观水平。分子生物学的不断进展,也使得一个新的学科脱颖而出,即分子人类学。这一学科的使命就是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通过研究人类DNA中所蕴藏的遗传信息来揭示整个人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分子生物学家在实验室用试管和其它仪器来推断人类进化的具体年代,从而将“人类非洲单独起源说”的核心理论扎实地构建在“DNA”基因分析之上。可以说,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都是“人类非洲单独起源说”的坚定支持者。
科学家告诉我们,每一种生物体之所以表现出各种形态学、生理学等方面的各种不同特征,都是由生物体内携带的被称为DNA的大分子化合物所发出的一道道遗传指令所决定的。这个DNA的大分子化合物,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基因。基因是决定事物发展进程和结果的基本决定因素。每个生命个体只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基因控制着每个生命个体的形态和行为,目的就是通过繁殖将它们自身遗传下去。基因的霸权,我们无法挑战。我们每个人其实仅仅只是基因延续的载体,被基因操控的傀儡。基因才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的主人,我们只是基因的奴隶。基因概念及其理论的建立,打开了人类了解生命并控制生命的窗口。
1953年4月25日注定是遗传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是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日。英国的《自然》刊登了沃森和克立克的合作研究成果: 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自DNA双螺旋结构问世以后,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基因的本质属性,即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断,包含着一个人所有遗传信息的片段,与生俱有,并终身不变。这种遗传信息就蕴含在每个人的骨骼、毛发、血液等所有人体组织或器官中。它记录每个人的生命演化,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一份历史记录,记录了一个生命的全部奥秘和隐私。DNA分子类似计算机磁盘,拥有信息的保存、复制、改写等功能。如果将人体细胞核中的23对染色体中的DNA分子连接起来拉直,其长度大约为0.7米;但若把它折叠起来,又可以缩小为直径只有几微米的小球。因此,DNA分子被视为超高密度、大容量的“分子存储器”。分析DNA的多态性,也就是破译人类演化的历史记录,可以向上追溯人类的祖先。这也就意味着:用DNA可以解决人种起源和繁衍分支的许多问题。
华夏子民的身份密码,就隐藏在我们携带的DNA之中。那也就是女娲或者说燧人氏给我们留下的“胎记”。我们出生时的“胎记”,早就镌刻在DNA的片断之中了。华夏文明的传世神话反复叩问的我们从哪里来的终极问题,其实答案就隐藏在我们身体内部的骨骼、毛发、血液之中。屈原在《天问》中发出的头两问,也就是“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个答案就隐藏在我们身体内部携带的DNA片断之中。这是华夏文明的诸位先贤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