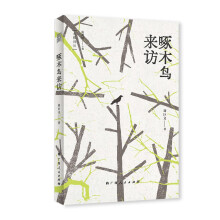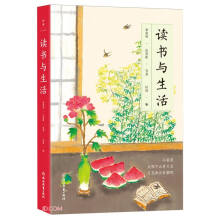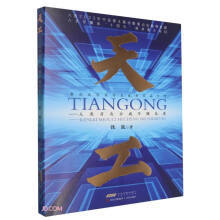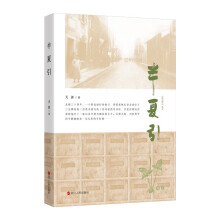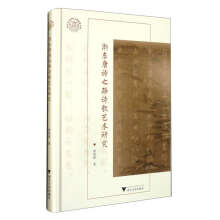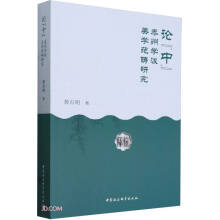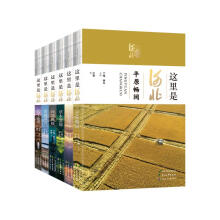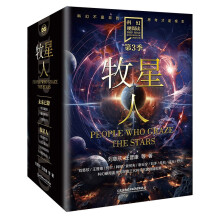《听歌放酒狂/启真·文史丛刊》:
“盼星星,盼月亮,来了太阳”——卑尔根日志
应该是整整10年前了,在杭州教工路上那家现早已消失的新民书店门口,为了动员童世骏教授把他老师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Skirbekk)教授的文集《时代之思》放到我和一位年长的同事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筹划的一套丛书中,我曾经在短信里“深情告白”:“如果减去10岁,我打算到卑尔根求学!”这诚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事实条件句,尽管其命题态度乃是无比真诚的!认真说起来,我与挪威哲学的因缘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当《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中译初版于1999年面世时,我还在为拙著《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中的《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对话》一章而殚思竭虑。而这本文集的两篇“压卷之作”,希尔贝克的《情境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实践的语用学与先验语用学的相互批判》和哈罗德·格里门(Harald Grimen)的《合理的分歧与认知的退让》,当时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在文中我曾隆重对之加以引用。在一种几乎不夸张的尺度上,我大概可以说是除挪威实践学传统在中文世界的“传人”之外,最早契合并受惠于这一学脉的中国学者之一。而且,自那以后,我还经常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和朋友圈里“宣扬”和“传播”挪威哲学。亦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挪威哲学文集》相隔十五六年之后在本人的推动下得以增订重版时,根据我的推荐,得到郁振华教授的支持,我的两位学生惠春寿和贺敏年承担了新增译文的翻译工作。而这次有机会访问挪威,正是因为贺君得到了CSC(China Scholalrship Council,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在卑尔根大学访学。cSC不但支持学生的访问计划,也同样支持访问学生的导师到该国该校访问。这是我继2007年普林斯顿之行后,时隔10年第一次出国,也许我还是该像前次那样,写下点儿什么,作为对自己严重不足的国际化程度之检讨和弥补?
因为有自己的学生会在湾城做向导和地陪,我在出发前自然就没有对此次行程做任何攻略。这种“不作为”的一个后果是,当我在浦东机场登上荷航的班机,得知飞到阿姆斯特丹需要11个小时,几乎想当场就晕过去。虽然我10年前曾经用15个小时飞到纽约,但这毕竟是10年前的事了。想到我的航班晚上11点多才离开上海,以目的地当地时间凌晨4点多抵达阿姆斯特丹,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红眼航班”上的漫漫长夜几乎让我不寒而栗。想象一下,在一个庞大的飞行物中,好几百号人戴着眼罩,蒙着被子,在此起彼伏的鼾声中,在黑夜里玩穿越,也确实让人有某种如同置身虚拟世界的荒谬感。稍可庆幸的是,荷航的伙食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在我记忆中也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样本可供比较),特别是凌晨3点多那份早餐可谓让人开了“洋荤”——这也是我平生吃过的最早的早餐!与10年前美航班机上清一色的老美不同,荷航班机上特意安排了3位中国空姐,这自然是为了让服务更到位,但是否也可以说是晚近10年吾国国力提升的显性标志?除了服从“自然必然性”之基本睡眠,在梦醒时分则有丹尼尔·加蒂(Daniele Gatti)指挥的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为我壮胆,那是荷航自身携带的装备,据说这位意大利指挥家刚于去年出任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当然这是我后来通过“度娘”才得知的!
在阿姆斯特丹等候转机的3个多小时里,我是在一种几乎没有自我感觉的极度空漠中度过的,只有在面对荷兰边检官时蹦出的“visitingscholar”两个单词赋予了我把自己从那个“一切皆流”的环境中分离出来的力量。本以为登上了早上8点半飞卑尔根的航班后自己的精神就会兴奋起来,却不料飞机离港没有多少分钟,我就开始困倦起来,想想大概是所谓的时差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吧。等到飞临湾城上空时,天已经在下雨,好在刚才阿姆斯特丹并没有下雨,否则或许也会发生《梵澄先生》中那个笑话的翻版:这雨真大,从阿姆斯特丹一直下到卑尔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