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湾?”柳建国凸出的颧骨兀地显露,他惊愕地问。
“过大寿,为的是让她老人家高兴。在这里办,她没几个熟人,来的人大多是应酬。”柳保华说,“我想,就在黄洋湾的‘和谐苑’搭个帐篷,杀上几口猪、羊、牛的,把几家亲戚和老邻居们都请上。不收礼钱,请个戏班子,好好红火两天。”
“大,您定吧。”柳建国抬起厚厚的眼皮凝视着大说,“我原想把奶奶的百岁大寿办得热闹隆重些。订上市里最好的酒店,请一些亲戚、高朋贵客、社会名流来捧个场,不过您这样想,也有道理。”
柳保华也是八十岁出头的人了。
六十五岁前,他是个农民,陌生的乡里人见到他都以为他是个城里人。因为他平时穿扮整齐干净,又有文化,能弹拉吹唱,脸上总带着笑意,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
六十五岁进城后。他感觉自己就是个草根,浑身散发着泥土味儿。尽管有很多人向他投来羡慕的眼神,但他晓得,那是当老板的儿子拥有的财富招惹来的,与他没有多少关系。他在这座城市里很难遇到个知音,只要他张嘴说话,那口浓重的陕北口音就把他与这座城市里的人截然分开。他习惯喝炒米奶茶,爱吃手把肉,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话,人们以为他是蒙古族。可是他在大街上偶尔遇到蒙古人,十有七八又不能用蒙古语流利地交流。他有时很郁闷,很寂寞,有空就往农村老家去。
这天,为筹备母亲的“百岁大寿”,柳保华在柳建国的陪同下,回到了黄洋湾。第二天,当太阳架在西北那片树林梢上时,他又来到那个岸边——
南北走向的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又向东而去。
他站在河堤上,手遮着眉弓,挡下刺目的阳光和寒风,向四下里张望。顺着东去的黄河望去。冰封的黄河在远处缩成一个亮点。在那亮点的尽头。黄河又掉头向南奔腾,在这里划出个巨大的“几”字,犹如一个问号。柳保华想:它要问甚?难道像那首民歌所唱的那样:“谁知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几十几道湾里有几十几条船……”
他看着枯竭萧条的黄河两岸,心中顿时有些失落。正要转身离开时,他的目光触碰到黄河上游的冰面,那冰面犹如点燃了时空倒回推进剂的火箭。顺着这条冰河轨道将他送回遥远的家乡——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黄河时的情景,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鬼子投降的前一天,那时他八岁。
那天是七夕,柳保华跟随大柳如海去古城赶集,保华妈出来送行。
他们三人站在门前的两棵老柳树下。这两棵柳树树干七扭八歪,树枝纠缠在一起,看不清上面的喜鹊窝究竟坐落在哪棵树上。保华妈不愿让他们出门,便说:“今儿会下雨的,牛郎织女见面时老天爷都会哭的。”
柳如海肩上挑起了一副货郎担子,抬头嘹了一眼刚爬上柳树梢的烧得通红的太阳,说:“银河都旱干了,天上哪来的雨呀?”说罢,一甩头说:“保华,走吧。”
保华妈发髻向后梳得溜光,穿着斜襟褂子,打着裹腿的裤脚下露出一双小脚。她就这样站在树下,一直看着他们父子的身影在山沟沟里矮下去,矮下去,直到丈夫头上扎着的白羊肚手巾消失在视线里。
柳如海挑着担子走在前面,或哼着小曲,或扯着嗓子唱信天游。他的脚步像踩着节拍,肩上的担子也有节奏地颤悠着。柳保华见他这副模样,很是稀罕。他打量着大的背影,高大结实的身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藏蓝色褂子,左右肩膀上各打着一块灰布补丁,下身穿一条黑裤子,吊在小腿中央。
他们走进了那条沟连沟、沟套沟、嘹不见尽头的山沟里。沟底不透风,柳保华走得大汗淋漓。柳如海放下担子,坐在一块石头上说:“保华,歇歇吧。”
柳保华圪蹴在大的跟前,见他从兜里掏出了旱烟锅,一边解开缠绕在烟锅和布袋子上的一截绳子,一边问:“保华,你哪天生的?”说着,他将烟锅头伸进布袋里挖烟叶,又用拇指隔着布袋在烟锅头的部位摁了摁。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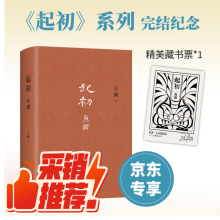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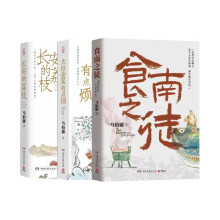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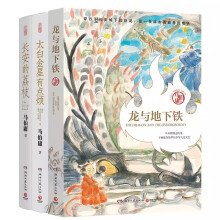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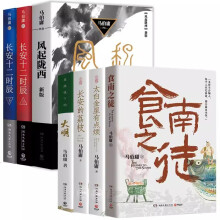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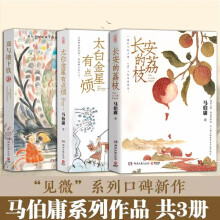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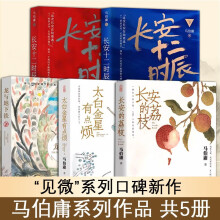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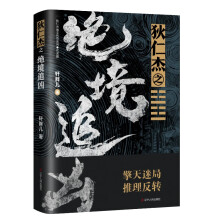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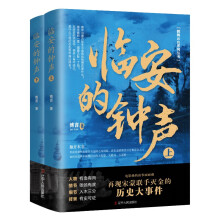

文本中闪耀着朴实、善良、真诚和豁达的人性底色,是一部深具家国情怀的长篇小说。
——《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授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