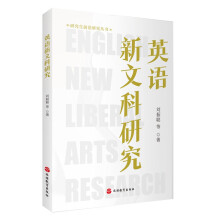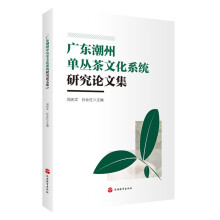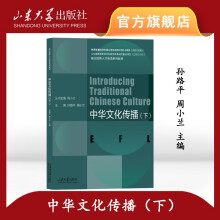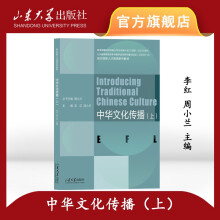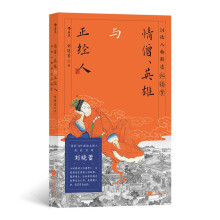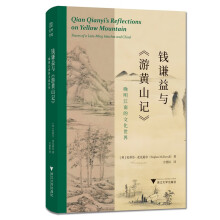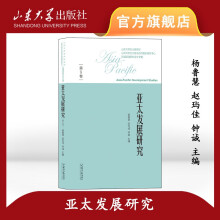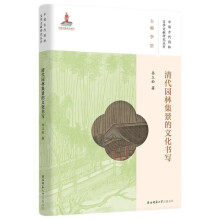《中国古代东北民族体育文化研究》:
民族文化继承性表现在其民族性和传统性的继承,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民族性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在内容、形式与文化内涵上具有独特性。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往往体现了特定民族的独特文化,其具体的运动方式、规则、肢体语言、习俗乃至礼仪,往往都具有唯一性甚至不可再生性,而其所蕴含着的思想、情感、意识和价值观也往往是难以被模仿和再生的。所谓传统的,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往往有着比较明显的传承性,它作为某一民族的重要文化内容,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被这一民族的成员自觉加以继承的,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发展延续的内在依据。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是各民族在其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行为技艺的凝练,也是各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在体能、智能表现形态中的结果。任何一个民族的体育项目,在发展中其行为模式和精神内涵得到人们的共识之后,就会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逐渐独立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得以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往往带有鲜明的本民族历史背景,也往往有着固定的形式与内容,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并不发生变化。一个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问题就是,随着历史潮流和时代背景的不断变迁,如果某一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之中却拒绝做出改变,其生存环境就会逐步趋向恶化,甚至走向衰亡。在改变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将其民族的和传统的精髓以一种新的方式和载体保存下来,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最理智的继承。这种理智就是要消除由其民族性而带来的地域性和排他性,也要消除由其传统性而带来的原始性和保守性。
通过对古代东北民族体育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我们发现,如鲜卑、契丹、蒙古、靺鞨、女真等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比较好地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清晰地看到,在这些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固守所谓的民族骄傲,而拒绝对自己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做出改变;他们并没有顽固地将所谓的民族传统视为禁脔从而排斥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吸收汉族体育的优秀项目与理念,使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如鲜卑族骑射体育活动,在充分吸收汉族射艺的精华之后,在文化内涵与竞技性、娱乐性上都得到了显著的增强,流传也越来越广,社会参与度逐步提高,源于游牧文化的骑射活动非但没有在农耕文化的传人后逐渐衰退,反而更加流行了。北朝时期,骑射活动已经不仅仅是鲜卑人的专利,而是在整个北朝社会中推行开来,从而打破了地域的桎梏。再如女真族的乐舞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在继承女真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融合了中原儒家思想和宗教舞蹈表现形式。在具体内容上,既有与敦煌乐舞、印度舞十分相似的中原宫廷乐舞,也有全真道教形式的乐舞,从而呈现了兼收并蓄、多元并存的发展姿态;蒙古族的宫廷乐舞则既有“征用旧乐于西夏”的记载,也有“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的过程,同样融合了多种风格,可谓继承传统风俗,兼容仪礼典制,从而呈现了互纳包容的审美特征。还有摔跤活动,历史上女真族的“拔里速”、蒙古族的“搏克”、满族的“布库”,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传统风格,但这些活动无一不是吸收了中原角抵的技术风格而对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加以改造,进而使民族体育文化大放异彩,这些都足以说明古代东北民族体育文化在融合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的显著特点。
其次,通过与汉民族先进文化的深入接触,这些民族对于体育活动的文化意义开始重视起来,统治阶层迅速地转变了其对待体育活动的观念,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其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开拓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从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承载了社会文化功能的竞技性活动,其娱乐性、竞技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才愈加受到人们的欢迎,并最终打破了民族的界限。体育观念的转变,使这些民族的传统体育开始顺应当时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潮流,将自身顺畅而从容地与当时的流行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在这一点上,鲜卑、契丹、渤海莫不如是。更为突出的表现则是到了后金社会和清王朝,在清入关以前,骑射、冰上活动等主要表现为军事和生产性质,是生活在冰天雪地、沃野林海的渔猎民族常见的生活方式,而当满族入主中原后,骑射和冰上活动非但没有因汉文化的介入而呈衰退势头,反倒被统治者作为大清国俗和国家恒制予以强力推行。其原因在于,当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活趋于稳定和安逸,体育与政治、军事的联姻,赋予了体育以全新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从而使民族体育文化在进步的社会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从民族体育文化本身而言,则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内生了自身的建设和完善的动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