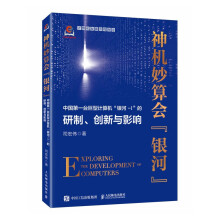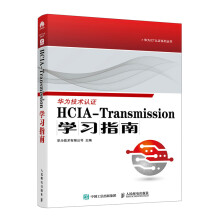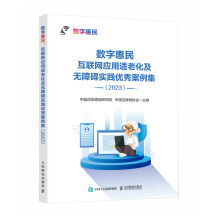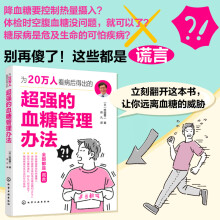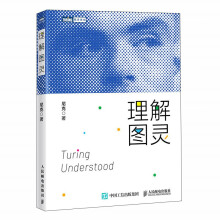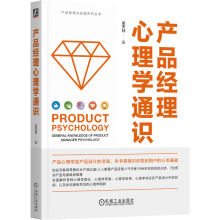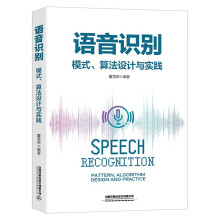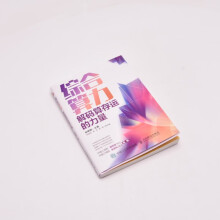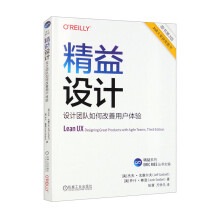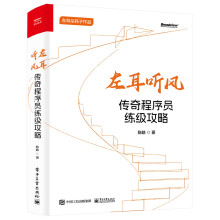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指出,“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基本、*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要以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契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 。范维澄(2016)认为,国家安全工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公共安全工作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安定有序和经济社会系统的持续运行为核心目标,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共安全领域的问题涵盖范围较广泛。根据我国刑法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义,公共安全指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及公共生产、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安全。按照*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特定”指的是公共安全的对象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而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公共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其后果具有严重性和广泛性,是行为人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根据范维澄(2016)的总结,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家公共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食品药品和违法犯罪等多个方面。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空间对国家公共安全逐渐呈现嵌入态势。于志刚(2014)认为,网络空间对国家公共安全的冲击主要体现为网络空间信息内容对于国家公共安全的碰撞与融合。伴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日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整体对于网络的依赖性快速增强,网络空间成为承载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工作生活的主要活动空间。因此,网络空间上的信息内容不断扩展,涉及国家公共安全问题的信息行为日益增多,这是信息社会发展的不可逆结果。Huang等(2007)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无论是个体有意识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发布,还是个体无意识的信息浏览和信息交换,都是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互联网信息行为。根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2017)的整理,各国的互联网上都存在着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网络邪教和迷信、网络谣言和诽谤、网络欺诈和非法交易、侵犯隐私和个人权益等在内的偏差互联网信息。按照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对公共安全的定义,对“特定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陈兴良,2013)。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把在网络空间中,可能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生产生活、社会安定和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严重影响的互联网信息行为,定义为面向国家公共安全的互联网信息行为,这些信息行为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网络色情和暴力、网络邪教和迷信、网络谣言和诽谤、网络欺诈和非法交易等方面。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 。方滨兴等(2016b)认为,由于网络空间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和扁平化的结构,各种在现实社会中被忽视、被弱化和被隐蔽的信息能够在网络中更迅速、更直接和更尖锐地传播。在很多时候,这些偏差互联网信息会溢出网络空间本身,和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意见互动叠加,使得网络空间中的舆情事件与现实空间中的实体事件相互作用,为这两类事件的处置都带来极大的复杂性。具体到国家公共安全而言,网络空间中的不当信息行为不仅能在网络空间中制造公众危机情绪和舆情事件,也能通过点燃公众危机情绪而导致或加重现实空间中的国家公共安全事件。2015年,网络空间安全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为国家一级学科,这标志着互联网信息对国家公共安全的嵌入态势已经得到高度的重视。
方滨兴(2016a)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都用行动表明,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的行为不仅应该符合公共秩序,而且还应该受到规则的约束。根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2017)的整理,各国的互联网上都存在着大量的偏差互联网信息,这些信息在很多时候对国家公共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自1996年“互联网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针对网络空间里的偏差信息进行了大量治理,具体体现为各种行政干预、法律规范、技术手段和专项行动等。虽然这些治理方法是绝对必要的,并且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得不承认,传统的互联网信息治理针对的都是互联网信息本身,没有考虑到互联网背后的网民。当前世界各国的互联网信息治理都是“治标”的方法,虽然它们实施简单、方法直接、见效迅速,但不得不承认,传统的互联网信息治理普遍存在着成本高、介入晚、反弹大等问题,因此,当前的互联网信息治理模式多是治标不治本的。可以看到,虽然世界各国都对互联网信息进行了大量治理,但各种偏差信息还是在网络空间中频频出现,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2017)。
德鲁克指出,包括管理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其*终目标都是要回归到人性和人心上来。本书认为,虽然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社会,但是网络空间中的网民是真实存在的“人”。每一个网络账号(ID)背后对应的都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人”是网络空间中任何活动的主体,互联网上的任何信息,都是个体信息行为的结果。因此,要达到对互联网偏差信息的“标本兼治”,其关键是要从浩瀚的互联网信息中跳脱出来,紧紧围绕着网络空间背后的“人”来展开。
1.2 融合治理的概念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所以,治理在网络空间中那些偏差信息行为(即在网络空间中发布、浏览和扩散前述可能对国家公共安全造成影响的不良的信息行为)背后的“人”,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是治理面向国家公共安全的互联网信息的根本方法,也就是说,对偏差互联网信息行为的有效治理,是通过治理这些信息背后的“人”来实现的。桂勇等(2015)对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类型的调查研究表明,在网络空间中有极端偏差情绪和信息行为的个体占少数,因此,对这部分人进行心理治理,是完全必要且可行的。因此,本质上,对偏差互联网信息行为的基础治理应该是一种以心理治理为基础、以法律治理为核心的融合治理模式,其目的是使用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方法,改变偏差互联网信息背后的“人”的偏差行为、认知和态度,让偏差互联网信息行为背后的“人”在心理上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
上述观念是契合治理理论的新发展的。通常,治理的模式被分为三类,即科层治理(hierarchical governance)、市场治理(market governance)和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李维安等,2014)。科层治理依靠的是等级权力,它通过限制不合作行为来使治理对象服从权威;市场治理依靠的是利益,它通过让个体的行为能够达到利益*大化来使治理对象配合;网络治理依靠的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团体、商业团体和公民个人等众多行为主体彼此合作,它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互利互惠和共同规范来使得治理对象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Bell等(2010)在过去三种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治理模式,即governance by persuasion,本书在此将其翻译为“劝导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强调的是转变治理对象的观念系统,使治理对象自觉地、自愿地、自发地按照治理主体的意愿行动,以此达到治理的目的。相比于其他三种治理模式,劝导治理是一种软性的、非侵入性的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可以采取各种方法,使治理对象在心理上接受并参与治理。
在劝导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根据英国卡梅伦政府的治理经验,提出了第五种治理模式,即nudging governance,本书在此将其翻译为“助推治理”。该治理模式的基础是认知缺陷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应该创造决策环境,引导个体自动做出有利于治理的行为。它与劝导治理的区别在于劝导治理是民众经过认知思考,自愿做出的行为改变,而“助推”则不经过认知思考,治理主体可以利用个体的认知规律,引导民众做出无意识的行为改变。卡梅伦政府于2010年在英国率先实践了助推治理模式,并在治理偏差行为上取得了良好效果(Jones et al.,2013)。
可以看到,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等模式在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治理中都有着广泛运用。根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2017)的整理,美国、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大量法律、采取了许多技术手段、进行了很多专项行动,并且各国和地区的互联网组织都与政府积极合作,对偏差的互联网信息开展了全社会的网络式治理。但是,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虽然这些治理方法实施简单、手段直接、见效迅速,但可以看出,目前的互联网信息治理普遍存在着成本高、介入晚、反弹大等问题,因此,当前的互联网信息治理模式多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前的治理模式都着重于偏差信息本身,而没有深入这些偏差信息背后的“人”的心理之中。本书认为,只有当偏差互联网信息行为背后的“人”的信念系统和治理主体保持一致,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行为才是真实的、自然的、持久的。因此,要真正地实现对偏差互联网信息的有效治理,其根本的目标并不是使这些信息消失,而是要使这些偏差互联网信息背后的信息行为和“人”的认知发生转变。
在这个思路下,“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改变和认知改变,是面向国家公共安全的互联网信息行为治理的根本目的。在融合了当前五种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本书结合我国的互联网环境和国家公共安全环境的特点,提出了第六种治理模式,即integration governance,本书在此将其翻译为“融合治理”。这种治理模式是以心理治理为基础、以法律治理为核心、以大数据技术为手段、以改变偏差互联网信息行为目标的治理模式。它是一种“治本为宗、标本兼治”的全新治理模式,其原理是通过多种策略,转变偏差互联网信息背后的“人”的偏差行为和心理认知,使得偏差互联网信息行为背后的“人”在心理上遵守相关法律,抵制偏差信息,从而让面向国家公共安全的互联网信息能够得到有效的、长期的、根本的治理。在本书中,融合治理模式是一种以政府为中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它与当前的治理模式并不是互斥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
融合治理模式的特点,就在于其“治本为宗、标本兼治”。要达到心理改变的目的,当前的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劝导治理、助推治理的思想和手段必不可少。融合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它并不是当前治理模式的简单混合,而是一个以心理治理为基础,以法律治理为核心,以大数据技术为工具,以偏差互联网信息行为背后的“人”的行为、认知和态度改变为目标的融合治理模式。在本书中,系统论提供了以心理治理和法律治理来融合各种治理模式的基本思维框架。在系统论中,系统内的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对面向国家公共安全的互联网信息行为进行有效的心理治理中,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是互联网信息治理中“看得见的手”,而劝导治理和助推治理则是互联网信息治理中“看不见的手”,融合治理模式就是要融合这些治理模式,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能够穿越屏障,紧紧地握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有效的治理体系。
对偏差互联网信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