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诗歌研究》:
二 现代性与汉语性
张枣曾主张把“现代性”辩争为“现代主义性”,即围绕“消极主体性”这一环球性现代主义文学核心意识形态及相关的种种现代主义诗学手法。可以认为,所有的诗学手法最终都将归结于语言手法,“没有出色的语言不可能有出色的文学”,“写作必将是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写作”。因而,文学的现代性即缔造“词语工作室”来呈现现代人的主体与心智,修复其受存在之恶侵袭的损伤。张枣坚持的是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也即,从短暂、消极、流行、黑暗的东西中提取出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制造出令人着迷之物——一种美学的积极,在鲁迅式的沉默或开口的诗学中即暗示着一种警悟的发光的主体对抗意识,把消极性化为美感,化成文本,以“言说的锋芒”成就“生存的锋芒”。对此,张枣亦以鲁迅的《立论》阐发“发声方式的困难即生存的困难”这一深刻思想。“词语工作室”的建构即关注在生存危机中诗歌如何可能。极端的美学原则由此浓缩为对语言即存在的语言本体论认识,可以说是诗歌现代主义性的根本写作姿态。不过,张枣异常警觉,他反思到,对诗歌的形而上学、元诗结构的全面沉浸——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纵使能够完成汉语诗歌对自律、虚构和现代性的追求,然而:“中国当代诗歌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既无独创性和尖端,又没有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原本,也就是说,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或日:它缺乏诗。”换言之,这仍然是复制了一种言说方式或诗学方案,而且是对精神文化实质迥然相异的另一地的复制。张枣在为北岛的诗集《开锁》写序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只关注写诗,写出一种尖端的诗,而不关注他是否在写汉语诗。”这一尖端包含经典现代主义的诗学手法,如非个人化的无地域“无自传”写作、“对外界物性的虚化和对词的通约化”。这一批评的言外之意即张枣所反思的元诗写作或日语言本体写作的悖谬:一种以词替物的狂欢与惰性,“语言原本”丧失了,写诗变成了符号布景与能指网里的循环。反之:“如果寻求把握汉语性,就必然接受洋溢着这一特性的整体汉语全部语义环境的洗礼,自然也就得濡染汉语诗歌核心诗学理想所敦促的写者姿态,即:词不是物,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也即,诗歌并非来自语言自足的幽闭,而是诞生在“词与物”的亲密拥抱与互动关系中,最高的理想即马拉美思考的“对外界物的摹写使物的自在性如此真实地体现,以致它与它的意念完全叠合,在这过程中,主体‘只是媒介,宇宙通过他而显形可见’”。词与物的关系即张枣在《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一文中提出的“现代性”与“汉语性”问题的关键。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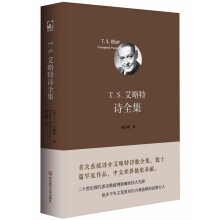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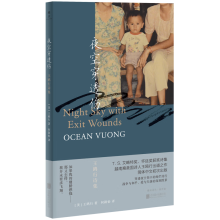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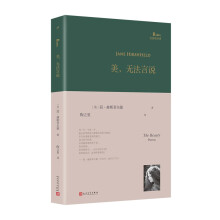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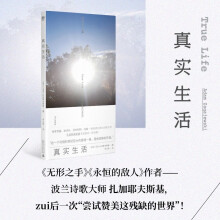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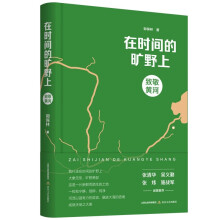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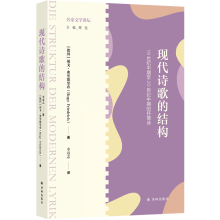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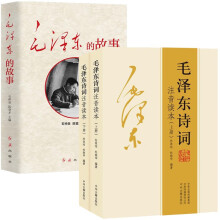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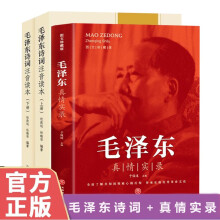
它是对汉语之诗的回归。……与其说张枣是二十世纪中国好的诗人之一,我更想说张枣是二十世纪深奥的诗人。
——顾彬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人中,一前一后,有两位技巧大师,一位是卞之琳,一位是张枣,写的都是精确的诗歌,比其他诗人考究太多,对诗的声音也格外敏感。
——江弱水
★在现代诗歌中,没有谁的语言亲密性达到张枣语言的程度,甚至在整个现代诗歌史上也找不到谁比他更善于运用古老的韵府,并从中配置出一行行新奇的文字。
——宋琳
★张枣是诗歌中的音乐大师。
——柏桦
★张枣是当代诗人中有诗学追求和研究难度的诗人。
——王光明
★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以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观并参悟博大精深的东方审美体系,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和熔点。
——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