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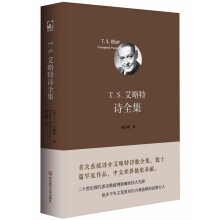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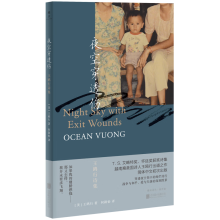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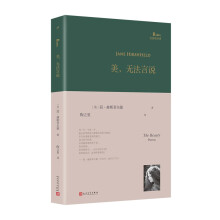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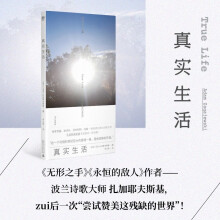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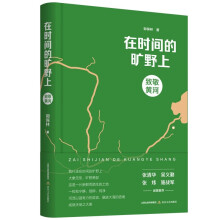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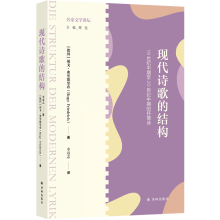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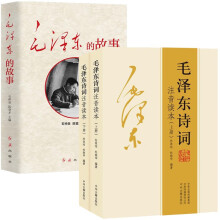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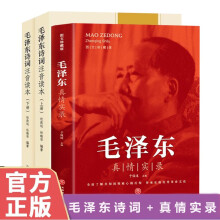
本集主要收录了诗词研究大家俞平伯先生对于先秦两汉魏晋诗歌的讨论和品鉴文章。主要分为两编,上编诗骚,谈的是《诗经》和《楚辞》,主体是谈《诗经》的《读诗札记》曾在1934年8月由北京人文书店单行出版;下编乐府,谈的是《羽林郎》《孔雀东南飞》和“古诗十九首”,主体是谈“古诗十九首”的《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本属于1935年4月为叶圣陶的《中学生》杂志作的随笔。可见,本集主要体现了俞平伯早期的诗词观点。
附]野有死麕之讨论
顾颉刚 胡适 俞平伯
一
《诗经》中有一部分是歌谣,这是自古以来就知道的。但因为从前的读书人太没有歌谣的常识,所以不能懂得它的意义。不懂得而竟要强做解释,这就不免说出外行话来了。我现在试举一个例。《召南·野有死麕》篇是一首情歌。第一章说吉士诱怀春之女,第二章说“有女如玉”,到第三章说道: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帨”,是佩在身上的巾。古人身上佩的东西很多,所以《诗经》中有“佩玉锵锵”“杂佩以赠之”的话。“脱脱”,是缓慢。“感”,是摇动。“尨”,是狗。这三句话的意思是:“你慢慢儿的来,不要摇动我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
出声音),不要使得狗叫(因为它听见了声音)。”这明明是一个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可怜一班经学家的心给圣人之道迷蒙住了。卫宏《诗序》云:“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郑玄《诗笺》云:“贞女欲吉士以礼来,……又吉士时无礼、强暴之男相劫胁。”朱熹《诗集传》云:“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辞,言姑徐徐而来,毋动我之帨,毋惊我之犬,以甚言其不相及也。其凛然不可犯之意盖可见矣!”经他们这样一说,于是怀春之女就变成了贞女,吉士就变成了强暴之男,情投意合就变成了无礼劫胁,急迫的要求就变成了凛然不可犯之拒!最可怪的,既然作凛然不可犯之拒,何以又言姑徐徐而来?我们现在在本集(《吴歌甲集》)第六十八首见到以下的歌词: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绕浜走过二三更,“走到唔笃场上狗要叫;走到唔笃窝里鸡要啼;走到唔笃房里三岁孩童觉转来。”“倷来末哉!我麻骨门闩笤帚撑,轻轻到我房里来!三岁孩童娘做主,两只奶奶塞仔嘴,轻轻到我里床来!”
顾颉刚
二
得适之师来信,指正我的《野有死麕》一段话,极快,今将原书录下:
颉刚:
你的《写歌杂记》很有趣味,今天的两条尤可爱。我因此想起我读《歌谣周刊》九一号时的一点感想,写出来寄给你:你解《野有死麕》之卒章,大意自不错,但你有两个小不留意,容易引起人的误解:(一)你解第二句为“不要摇动我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二)你下文
又用“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字样,这两句合拢来,读者就容易误解你的意思是像《肉蒲团》里说的“干哑事”了。“性的满足”一个名词在此地尽可不用,只说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就够了。“帨”似不是身上所佩,《内则》“女子设帨于门右”,似未必是“佩巾”
之义。佩巾的摇动有多大的声音?也许“帨”只是一种门帘,而古词书不载此义。《说文》“帨”字作帅,“事人之佩巾”
如何引申有帅长之义?《野有死麕》一诗最有社会学上的意味。初民社会中,男子求婚于女子,往往猎取野兽,献与女子。女子若收其
所献,即是允许的表示。此俗至今犹存于亚洲、美洲的一部分民族之中。此诗第一、第二章说那用白茅包着的死鹿,正是吉士诱佳人的贽礼也。
又南欧民族中,男子爱上了女子,往往携一大提琴,至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以挑之,吾国南方民族中亦有此风。我以为《关雎》一诗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亦当作“琴挑”解。旧说固谬,作新婚诗解亦未为得也。“流之”“求之”“芼之”等话皆足助证此说。
研究民歌者当兼读关于民俗学的书,可得不少的暗示。
如下列各书皆有用:
Westermarck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and Practice.Hobhouse: Morals in Evolution.
适 十四,五,廿五
我诚实的招认,我是误解了。帨为门帘,现在虽没有坚强的证据,但未始不可做一个假设,徐待证据的发见。本集第二十四首云:长手巾,挂房门
短手巾,揩茶盆,揩个茶盆亮晶晶。上一句大有《内则》“设帨于门右”之意,下一句似是抹布。那么,在这两句中,这“手巾”一名就有了歧义了。又苏州人叫擦面布亦为“手巾”,则此名竟有了三义。帨在佩巾之外别有意义,自属可能。适之先生又对我说:“此诗之义,经学家虽讲为峻拒,文学家却是讲为互恋的。记得王次回诗中即有此类句子。”我依了这个指导,去寻《疑雨集》,在第四卷《无题》诗中得到以下一首:
重来絮语向西窗,奉坠罗衣泪一双。臂钏夜寒归雪砌,鬓鬟风乱过春江。金堂地逼防言鸟,茅舍云深绝吠尨。郎肯爱闲须一到,阿家新醊正开缸。
顾颉刚
三
颉刚兄:
读你的《写歌杂记》第七关于《野有死麕》的卒章(《歌谣周刊》第九四号),我略微有几句话想对你们饶舌。你的原文,文字上微有疵病,适之先生所正极是,兄亦自承认了。至于释“帨”为佩巾,我意已是解此章之义,正不必别求歧义。如适之先生说:“佩巾的摇动有多大的声音?”这可以回答,实没有多大的声音。但是门帘的摇动又有多大的声音呢?何必多此一举?我先就“帨”研究,再就本章之意推
合之。“帨”之训为门帘只是一种想象,你们都已明言之。就《礼记》本文上看:“男子悬弧于门左,女子设蜕于门右。”“帨”之非门帘实明甚。只因为弓矢是男子常佩之物,巾帨是女子常佩之物,故悬之于门侧,且别左右,以作男女诞生之象征。若帨为门帘,则悬在门中乃事理之常,何必特设之于门右乎?更有何象征之意味乎?就上文推之,男子既佩弧,何以女子不可佩帨?至于你说:“帨在佩巾之外别有意义自属
可能。”可能原是可能的,只是不必多此一举耳。况且,即使别有意义,安见其为门帘呢?手巾在俗语中有手帕、擦面巾等等歧诠,诚如尊言;但却不可推之帨与门帘之间,因为小手巾与大门帘太悬殊了。足下以为然否?故若就《礼记》而论,“帨”决非门帘。就《诗经》而言,亦不见其为门帘。且无论是门帘也罢,手帕也罢,摇来摇去,总不见得有多大的声音。你们两位考据专家在此都有点技穷了。我对此章作解,微与您俩不同。我以为卒章三句,乃是一口答应,岂不大杀风景呢?“将军欲以巧示人,盘马弯弓故不发”,急转直下式的偷情与温柔敦厚之《诗·国风》,得无
大相径庭乎?一笑!
弟平伯 六月九日
目 录
第一编 诗骚编
诗的歌与诵(两篇)
读诗札记
自 序
一 周南·卷耳
二 召南·行露
三 召南·小星
四 召南·野有死麕
五 邶·柏舟
六 邶·谷风
七 邶·北门
八 邶·静女
九 鄘·载驰
屈原作品选述
第二编 乐府编
说汉乐府诗《羽林郎》
谈《孔雀东南飞》及其古诗的技巧
一 略谈《孔雀东南飞》
二 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技巧
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
一 行行重行行
二 青青河畔草
三 青青陵上柏
温馨提示:请使用德清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