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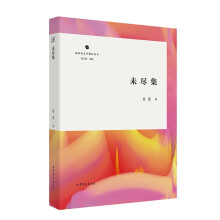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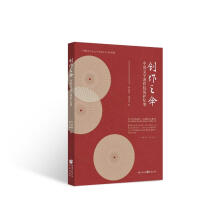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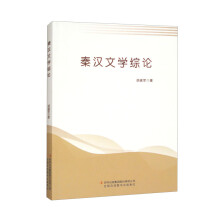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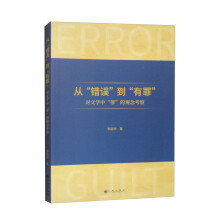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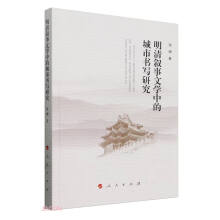




本书从中西方古典戏剧互为参照的宏阔视野出发,运用比较对照的研究方法,滤取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为具体研究对象,从“停叙”、“幕后戏”、“预叙”、“发现”与“突转”几个论题切入,以解读大量戏剧文本为依据,尝试就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叙事技巧展开专题性的比较研究。
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中的“发现”与“突转”“发现”与“突转”,是源自西方戏剧美学范畴的两个重要概念术语。中西古典戏剧艺术尽管特色纷呈,各有千秋,然其在戏剧创作的基本理念与叙事技巧诸方面,却又每每存在着颇多相似、相通、相同之处。如果浏览一番中西古典戏剧作品,我们将不难看出,“发现”与“突转”确乎是普遍存在于中西古典戏剧创作实践中的,为大多数剧作家惯常用以安排情节、结构布局的客观事实。有鉴于此,本章尝试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有关“发现”与“突转”的理论为依据,以古希腊戏剧为参照,以元杂剧为审察对象,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切入,拟就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运用“发现”与“突转”之问题略陈管见。一、“发现”与“突转”界说《诗学》是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针对业已高度繁盛的古希腊戏剧(主要是悲剧)艺术成就与创作经验,给予系统化梳理总结的一部理论巨著。它所总结和概括出的许多理论原则,对后世西方戏剧创作产生重要指导、借鉴作用与深远影响力。其中,“发现”与“突转”便是亚氏对古希腊戏剧家在结构布局、安排情节方面成功使用的独特叙事技法的准确把握与精辟阐释。作为深入探究有关问题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很有必要首先对“发现”与“突转”这两个关键词语,予以一番追根溯源的诠释、梳理、廓清与阐发。何谓“发现”?亚里士多德以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两部悲剧为例证,在《诗学》第十一章里指出:“‘发现’,如字义所表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或仇敌关系。”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4(陈中梅译本将这段话译为:“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9)《俄狄浦斯王》讲述忒拜国王夫妇拉伊俄斯与伊俄卡斯忒慑于“杀父娶母”之神谕,将襁褓中的儿子交由牧羊人扔到山里喂狼。出于怜悯,牧羊人违令将婴儿托付给邻国科林斯国王的牧羊人。尚无子嗣的科林斯国王玻吕玻斯夫妇将“弃婴”立为王子收养,取名俄狄浦斯。成年后的俄狄浦斯得知了“杀父娶母”的神谕,为躲避这一可怕厄运而离家出走。他在边境先是失手打死周游巡视的拉伊俄斯,随后因消除祸害忒拜的妖怪斯芬克斯而被拥戴为新国王,按惯例娶了寡后伊俄卡斯忒为新王后。至此俄狄浦斯的厄运,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应验。上述“杀父娶母”这一核心事件被剧作家隐藏于幕后做了“暗场”处理,悲剧故事开始于俄狄浦斯登基16年后,中心情节是俄狄浦斯调查先王凶杀案。剧情中至为关键的环节在于报信人——科林斯国王的牧羊人乙,他是前来向俄狄浦斯通告科林斯国王玻吕玻斯驾崩噩耗、请求俄狄浦斯回国继位的信使。为打消俄狄浦斯对“娶母”(自己返回科任托斯必须娶寡后为新王后)的担忧,向他坦言科林斯国王夫妇并非其生身父母。这番无意之中说出的劝慰话可谓石破天惊,经由当年“弃婴”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忒拜前国王牧羊人甲的举证,恰恰披露出俄狄浦斯的身世,导致“忒拜老王被杀”血案真相大白。由此,俄狄浦斯与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夫妇之间的父(母)子血缘关系及其“杀父娶母”内幕昭然若揭,无情地将悲剧主人公——那位万民拥戴的贤明国君俄狄浦斯,推至毁灭的绝境。《伊菲革涅亚在陶里克人中》则讲述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儿女瑞斯特斯与伊菲革涅亚的故事。当年为平息海神之怒而使希腊战船顺利出海,联军统帅阿伽门农被迫将女儿伊菲革涅亚作为祭品宰杀。行刑之际,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用一只母鹿偷偷替换下伊菲革涅亚,并将她送到黑海北边的异域他乡陶里克安身。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亚凯旋的当夜,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伙同奸夫埃葵斯托斯,以“为无辜的女儿伊菲革涅亚报仇”为由,将丈夫残忍地谋杀于浴缸内。该剧主要情节是俄瑞斯特斯为父复仇而杀死母亲,为躲避复仇女神的迫害而逃到陶里克海边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前栖身。身为神庙祭司的伊菲革涅亚不知他的底细,筹划将这个“外乡人”当作供奉神庙的祭品杀掉。后来经过正面接触与询问对证,方得悉其真实身份——原来竟是自己的亲弟弟。“姐姐与弟弟”这一特定人物关系的“发现”,遂使一场流血悲剧得以及时避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着意强调“发现”的实质,在于某种特定人物关系(此人物关系往往又与人物具有某种特殊身世、身份密不可分):“‘发现’乃人物的被‘发现’,有时只是一个人物被另一个人物‘发现’,如果前者已经识破后者;有时双方须相互‘发现’,例如送信一事使俄瑞斯特斯‘发现’伊菲革涅亚是他姐姐,而俄瑞斯特斯之被伊菲革涅亚承认,则须靠另一个‘发现’。”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5(陈中梅译本将这段话译为:“既然发现是对人的发现,这里就有两种情况。有时,一方的身份是明确的,因此发现实际上只是另一方的事;有时,双方则需互相发现。例如,通过伊菲革涅亚托人送信一事,俄瑞斯忒斯认出了她,而伊菲革涅亚则需另一次发现才能认出奥瑞斯特斯。”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9)也就是说,特定人物关系的发现存在着“单向性”与“双向性”两种类型。前者属于一方对另一方的发现,即人物甲知晓人物乙与自身所具有的或亲属或仇敌等关系,反之亦然。它以某一单方知晓对方与自身具有亲属或仇敌之特定人物关系为前提。后者属于双方事先互不知晓各自底细,而以一定的机缘为条件,最终得以彼此间知晓或亲属或仇敌的特定人物关系。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索福克勒斯的《埃勒克特拉》、欧里庇得斯的《埃勒克特拉》等,均以俄瑞斯特斯为了给父亲阿伽门农复仇而杀死母亲的故事为题材。三部剧作中俄瑞斯特斯复仇目标明确——躲在暗处的他知道克吕泰墨斯特拉及其奸夫埃葵斯托斯的底细,但由于他的巧妙伪装和故意隐瞒,对方根本无法知晓他的底细。等到“发现”俄瑞斯特斯真实身份之际,她(他)们随即倒在死亡的血泊中了。大概由于上述三剧里这种“单向性的发现”在古希腊悲剧中较为常见,所以亚里士多德没有论及。但针对“双向性的发现”,亚里士多德则列举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予以说明。该剧女主人公伊菲革涅亚生活于黑海北边的陶里克,其身份是当地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寺庙的女祭司。陶里克国王抓住两个来自异乡的希腊人,按照以异邦人为祭品的宗教习俗交由她杀献祭神。伊菲革涅亚决定杀掉其中一位俘虏(即俄瑞斯特斯),释放另一个俘虏回希腊替她送信,告知弟弟俄瑞斯特斯设法速来救她回归故土。由于担心送信人可能会将信遗失,她特地将信的内容念给他听。在一旁等候被宰杀的俄瑞斯特斯因此偶然机遇,恍然得知女祭司正是自己尚在人世的姐姐伊菲革涅亚。不过随后剧情里伊菲革涅亚认出俄瑞斯特斯,颇费了一番周折。俄瑞斯特斯依次说出许多确凿的物证,诸如伊菲革涅亚当年织布上的图案特征、放在闺房里的古矛等,伊菲革涅亚据此得以确认:对方正是自己朝思暮盼的弟弟俄瑞斯特斯。人物行动与人物关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以及会产生怎样的戏剧效果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四章里分析指出:“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哪些行动是可怕的或可怜的。这样的行动一定发生在亲属之间、仇敌之间或非亲属非仇敌的人们之间(即戏剧行动的发生不外乎三种人物关系)。如果是仇敌杀害仇敌,这个行动和企图,都不能引起我们的怜悯之情,只是被杀者的痛苦有些使人难受罢了;如果双方是非亲属非仇敌的人,也不行;只有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才行,例如弟兄对弟兄、儿子对父亲、母亲对儿子或儿子对母亲施行杀害或企图杀害,或做这类的事——这些事件才是诗人所应追求的。”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4遵循上述原则,亚里士多德深入细致地辨析了戏剧家取材流传故事或者自行虚构故事时,可能出现的人物行动三种方式的适宜度与优劣性。最糟的是知道对方是谁,企图杀他而又没有杀——这样只能使人厌恶(即明知对方是自己的亲属而企图杀他,会让人起反感),而且因为没有苦难事件发生,不能产生悲剧的效果;因此没有什么人这样写作,只是偶尔有人采用,如《安提戈涅》剧中海蒙之企图杀克瑞翁。次糟的是事情终于做了出来(明知对方是亲属而把他杀了)较好的是不知对方是谁而把他杀了,事后方才“发现”——这样既不使人厌恶,而这种“发现”又很惊人。……最好的是最后一种(即不知对方是谁而把他杀了的所谓“较好”的第三种),如在《克瑞斯丰忒斯》(已经失传)剧中,墨洛珀企图杀她的儿子,即使“发现”是自己儿子而没有杀;又如在《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剧中,姐姐及时“发现”她的弟弟(而终止欲将弟弟杀死祭神的行动);再如在《赫勒》(已经失传)剧中,儿子企图把母亲交给仇人,却及时“发现”是他的母亲。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5—46那么,“发现”有哪些种类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六章中作出了具体划分。第一种是由标记引起的“发现”。这种方式最缺乏艺术性,无才的诗人常使用。标记有生来就有的,也有后来才有的,包括身体上的标记(如伤痕)和身外之物(如项圈,又如《堤洛》剧中的摇篮,剧中的“发现”便依靠这摇篮)。第二种是诗人拼凑的“发现”。由于是拼凑的,因此也缺乏艺术性。例如在《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剧中,俄瑞斯特斯是他自己透露他是谁;至于伊菲革涅亚是谁,是由一封信而暴露的;而俄瑞斯特斯是谁则由他自己讲出来,他所讲的话是诗人要他讲的,不是布局要他讲的。第三种是由回忆引起的“发现”。由一个人看见什么,或听见什么时有所领悟而引起的。如狄开俄革涅斯的悲剧《库普里俄人》剧中的透克洛斯是他自己看见那幅画而哭泣,在阿尔喀诺俄斯故事中,俄底修斯听见竖琴师唱歌,因此回忆往事而流泪,他们两人因此被“发现”。第四种是由推断而来的“发现”。如《奠酒人》剧中的推断:“一个像我的人来了,除俄瑞斯特斯而外,没有人像我,所以是他来了。”此外,还有一种复杂的“发现”,由观众的似是而非的推断造成的。如在《俄底修斯伪装报信人》(已经失传)剧中,俄底修斯说,他能认出那把弓——实际上他并没有见过那把弓,观众以为俄底修斯会这样暴露他是谁,但这是错误的推断。一切“发现”中最好的是从情节本身产生的,通过合乎可然律的事件而引起观众的惊奇的“发现”。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和《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中的“发现”:伊菲革涅亚想送信回家,是一桩合乎可然律的事。唯有这种“发现”不需要预先拼凑的标记或项圈。次好的是由推断而来的“发现”。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1—54概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上述各种“发现”中,最好的“发现”乃是“从情节本身产生的”(即第五种),极其赞赏这种尽量摒弃纯粹偶然性(第一种)或主观随意性(第二种)等因素,在情节的发展进程中依循可然律而自然产生出来的“发现”,就像《俄狄浦斯王》中“杀父娶母”内幕的“发现”那样,“通过合乎可然律的情节引起观众的惊奇”。同时亚氏又从有机联系的视角出发,强调这种最好的“发现”应当与“突转”紧密契合:“发现”如与“突转”同时出现例如《俄狄浦斯王》剧中的“发现。”,为最好的“发现”。它属于与情节,亦即行动最密切相关的“发现”,因为那种“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的时候,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按照我们的定义,悲剧所模仿的正是能产生这种效果的行动,而人物的幸福与不幸也是由于这种行动。次好的“发现”则属于那种由推断而来(即第四种)的“发现”。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1—54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我们可以力求完整准确地来界定“发现”的含义及其特征:“发现”系指戏剧中尚未被人们(剧中人物或观众;相对而言主要针对剧中人物而言)知晓的某些特定人物关系,以及某些事件内幕的披露与挑明。人物关系与事件内幕比较之下侧重于前者,换言之,“发现”主要针对某些特定、特殊人物关系而言。正如《俄狄浦斯王》中“杀父娶母”内幕的披露,须首先依赖于俄狄浦斯真实身份(即身世)的暴露。因为若无俄狄浦斯与先王及王后血缘亲情之人物关系的彰显,其“杀父娶母”内幕仍将潜形匿影,可能永远不会为人知晓。那么,何谓“突转”呢?亚里士多德仍以《俄狄浦斯王》为例,在《诗学》第十一章中将“突转”解释为: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这种“突转”,并且如我们所说,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方式,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而发生的。如在《俄狄浦斯王》剧中,那前来的报信人在他道破俄狄浦斯的身世,以安慰俄狄浦斯,解除他害怕娶母为妻的恐惧心理的时候,造成相反的结果;又如在《林叩斯》剧中,林叩斯被人带去处死,达那俄斯跟在他后面去执行死刑,但后者被杀,前者反而得救——这都是前事的结果。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3—34这里仅对亚里士多德引以为证的《俄狄浦斯王》稍予解读。剧中报信人——前来传达科林斯国王驾崩消息的牧羊人,正是当初直接从忒拜国王牧羊人手里收养“弃婴”的那位好心者。原本出于消除俄狄浦斯担忧犯下“杀父娶母”罪孽的恐惧心理而加以劝慰,孰料“事与愿违”:他无意之中所说的一番劝慰话,经由当年违令未将“弃婴”处死的知情者——忒拜国王拉伊俄斯牧羊人——的出面作证,恰恰披露出俄狄浦斯的真实身份。科林斯国王夫妇不过是俄狄浦斯的养父母,忒拜国王夫妇才是其生身父母!戏剧情势由此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惊天大逆转:俄狄浦斯从处于主动追查杀害先王凶手的顺境,陡然跌入被动尴尬且无可逃遁的逆(绝)境中,不得不去承受因“杀父娶母”罪责而招致的严厉惩罚!亚里士多德将悲剧中主人公从顺境到逆境或者从逆境到顺境的境遇转换,具体分为“渐变”式与“突转”式两种。其一,“在简单的情节中,由顺境到逆境或者由逆境到顺境的转变是逐渐进行的,观众很早就感觉到这种转变”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3(注释①)。对此笔者试以埃斯库罗斯悲剧《阿伽门农》中阿伽门农命运的转变为例。该剧从开幕时守望烽火台哨兵忧郁心态的渲染,到长老们对不祥之兆的预感,再到王后克吕泰墨斯特拉表面奉承背后磨刀霍霍的计谋,再到身为女俘、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对自身及其主人阿伽门农即将遭遇卑鄙谋杀的悲惨命运的预言……可以说,凯旋的希腊英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从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便一步步向着死亡的陷阱滑行,对此观众早已心知肚明。于是,随后阿伽门农被谋害死于浴缸的结局,在如此一种循序渐进的“渐变”式剧情发展进程中水到渠成。这种“渐变”不属于“突转”的情形。其二,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的是下面另一种情形,即有一些转变是突然发生的。由顺境到逆境或者由逆境到顺境的转变是一种形式“突转”,在复杂的情节中,主人公一直处于顺境或者逆境中,但到某一“场”里情势突然转变,这种“突转”须合乎可然律或者必然律,即事件的发生须意外但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3(注释①)即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那样,导致俄狄浦斯从追查凶手的顺境陡然坠入沦落为凶手的逆境的“突转”,始于报信人科林斯国王牧羊人的一番劝慰话。这种“突转”非常出人意料,却又因符合因果律而合乎情理之中。即出于消除俄狄浦斯“娶母”之不必要顾虑的好心,牧羊人才会披露刚刚驾崩的科林斯国王玻吕玻斯只是俄狄浦斯养父的隐情。同时又由于这位牧羊人正是当年从忒拜老王拉伊俄斯牧羊人手中收养弃婴的当事人与知情者,为了验证自己所说劝慰话的真实性,报信人要求与忒拜国王牧羊人对质,自然引出后者无法回避的出面作证。两位当事人兼知情者的聚会,令俄狄浦斯的身世之谜不可避免地曝光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上述阐释,我们同样可以力求完整准确地来界定“突转”。“突转”是指戏剧情节在其发展进程中依循可然律或必然律的因果逻辑,而产生的“从顺境到逆境”或者“从逆境到顺境”的突然变化与重大转折。因其着意于情节发展的那种突发性逆向变异,故主要限于情节范畴。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突转”运行轨迹的描述——“从顺境到逆境”(一般指悲剧)或者其“从逆境到顺境”(一般指喜剧),显然是不够完备的。当然主要原因在于客观历史的局限性,因为当时还没有悲喜剧、正剧等悲剧、喜剧之外其他类型戏剧正式出现,所以不应对亚里士多德求全责备。笔者以为,“突转”至少应包含三种运行轨迹:一是“从顺境到逆境”的悲剧性突转,多见于悲剧;二是“从逆境到顺境”的喜剧性突转,多见于喜剧;三是“从顺境到逆境”与“从逆境到顺境”交互发生的“悲喜交错性”突转,多见于悲喜剧、正剧等。同时,“突转”无论是“从逆境到顺境”或者“从顺境到逆境”,其运行轨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仅为总体模式的泛泛而谈,未能就“突转”的具体运行过程展开更详尽的论述。“突转”的实际运行过程无疑应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其间会融含着许多大小不等的更趋细微具体的环节。尤其在那种根本性的逆转即“突转”发生之前,一定还存在着某些分量不等、起到铺垫过渡、推波助澜作用的转变。相对于一百八十度转折、突变的“大逆转”或“大顺转”而言,我们不妨可称其为“小逆转”或“小顺转”。由此我们对“突转”的运行轨迹作如下描绘,也许更完善齐备:其一,顺境—小逆境—大逆境(即突转性的逆境);其二,逆境—小顺境—大顺境(即突转性的顺境)。另外,关于“突转”一词的译名,笔者亦感到尚有规范化的必要性。鉴于“突转”造成的情节发展往往与观众的预料猜测相反,所以称“逆转”未尝不可。还有些学者采用“转变”“突变”之类的名称,因不违背亚里士多德原文中的基本含义,自然亦不无道理。但推敲之下,笔者以为仍以“突转”一词最为准确妥当。因为它既能彰显“突发性、突然性”的那层含义(“逆转”或“转变”一词明显缺乏此层含义),又强调突出了某种“变化”:“转”中必然有“变”,而“变”中未必一定有“转”(尤其是“大转”),就像某些无碍大局的细微变化那样。因此较之“突变”一词更胜一筹。二、“发现”与“突转”在古希腊戏剧中的运用在视“情节”为戏剧核心要素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与“突转”的问题与“情节”须臾不能脱离。由此他能够敏锐地从对“情节”之简单或复杂的分类中,深入探讨“情节”与“发现”或“突转”的关系。即如其在《诗学》第十章里所指出的:“情节有简单的,有复杂的;因为情节所模仿的行动显然有简单与复杂之分。所谓‘简单的行动’,指按照我们所规定的限度连续进行,整一不变,不通过‘突转’与‘发现’而到达结局(指由逆境转入顺境,或者由顺境转入逆境的结局)的行动;所谓‘复杂的行动’,指通过‘发现’或‘突转’,或通过此二者而到达结局的行动。但‘发现’与‘突转’必须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出来,成为前事的必然的或可然的结果。两桩事是此先彼后,还是互为因果,这是大有区别的。”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2笔者以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其实已经道出了“发现”或“突转”与“情节”之间的三种构建模式:其一是只有“发现”而无“突转”,亦即没有引起“突转”;其二是只有“突转”而无“发现”,亦即引起“突转”的原因并不在于“发现”;其三则为既有“发现”又有“突转”。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八章里将悲剧划分为复杂剧、苦难剧、性格剧和穿插剧四种类型时,亦同样关注到“发现”与“突转”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复杂剧完全靠“突转”与“发现”构成(笔者对此理解为“突转”与“发现”构成“复杂剧”),但“复杂剧”中可能还有其他“成分”。比如,最重要的成分首先即为“发现与突转”(亚里士多德这里将两者合为一个成分),其次是“苦难”,再次是“性格”,最后是“穿插”。“穿插”最不重要,但“穿插”若挑选、安排得当,也可以构成一出不错的戏剧。如欧里庇得斯悲剧《特洛亚妇女》中的“穿插”,均与王后赫卡柏的“苦难”有密切关系。一部戏剧里可能运用上述四个成分,或者只利用四个成分中的两三个。如,《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中便运用了四种成分:它属于一出“复杂剧”,其中有“发现”与“突转”,但剧中也有“苦难”(指俄瑞斯特斯面临被杀献祭之危险),也有“性格”(俄瑞斯特斯选择死,即甘愿被杀献祭),还有“与主人公相结合”的“穿插”。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9—60,60—61(注释④)根据亚里士多德上述关于“简单情节”(或“复杂情节”)与“发现”(或“突转”)之间存在多样化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大量古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从中梳理归纳出运用“发现”或“突转”的几种主要类型。其一,既没有“发现”也没有“突转”,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普罗米修斯》。该剧主要剧情为宙斯当初依赖普罗米修斯的帮助,推翻父亲克洛诺斯而获得王权。掌权后的他变得专横暴虐,仇视并欲毁灭人类。
引论
一、“代言体”、“叙述体”与戏剧之关系辨析
二、元杂剧文本体制的叙事性解读
三、中西方古典戏剧叙事学渊源回顾
四、戏剧叙事学发展概况与研究现状扫描
五、研究思路、方法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章 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中的“停叙”
一、“停叙”概念界说
二、中西古典戏剧话语模式比较
三、元杂剧中“停叙”之运用及其探因
四、“停叙”在古希腊戏剧中的运用及其探因
第二章 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中的“幕后戏”
一、“幕后戏”、“幕前戏”、“前史”辨析
二、“战争”与“死亡”: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运用“幕后戏”之异同
三、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重视运用“幕后戏”探因
第三章 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中的“预叙”
一、“预叙”界说
二、“预叙”在元杂剧中的运用及其探因
三、“预叙”在古希腊戏剧中的运用及其探因
第四章 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中的“发现”与“突转”
一、“发现”与“突转”界说
二、“发现”与“突转”在古希腊戏剧中的运用
三、“发现”与“突转”在元杂剧中的运用
四、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重视运用“发现”与“突转”探因
结语
附录
表一 古希腊戏剧运用“三一律”情况统计表
表二 元杂剧主唱人情况统计表
表三 古希腊戏剧运用“幕后戏”情况统计简表
表四 元杂剧与“三一律”关系抽样分析统计表
参考文献
温馨提示:请使用德清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