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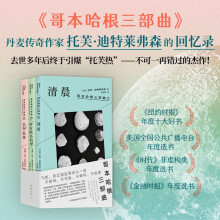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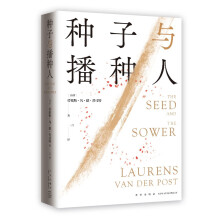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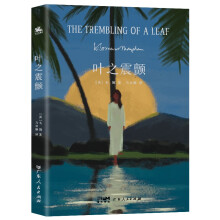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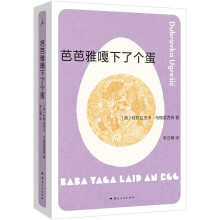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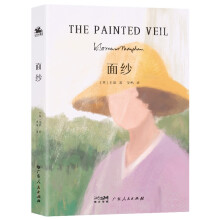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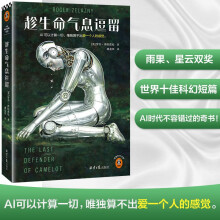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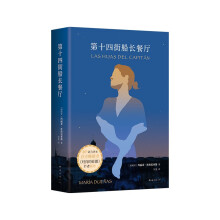

第一章现在,注意了!
“某次,一个温顺、正直的人
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
从此便向着死亡之谷走去。”
到了这个年纪、状态,每晚睡前我都得好好洗干净脚,做好半夜随时有可能被抬上急救车的准备。
如果那晚我查了星历,知道天象,肯定不会就此睡去。然而我偏偏喝了些助睡眠的酒花茶,还吃了两片安定,睡得很沉。因此,当半夜不祥的急促敲门声将我惊醒时,我久久缓不过神来。我跳下床,站在床沿,飘忽不定,颤颤颠颠。惊魂未稳、尚未被唤醒的身体难以从纯真的梦里回到现实。我踉跄蹒跚,似乎就要失去意识一般。因为病情的关系,z近我常常这样。于是,我强迫自己坐下,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我在家,现在是晚上,有人敲门。”这样才终于控制住精神状态。在黑暗中找寻拖鞋时,我听到敲门的人正绕着屋子走,嘴里还嘟囔着些什么。此时我正想着楼下的电表盒里有一罐防身喷雾,这是迪迦给我用来防偷猎者的。我在黑暗中找到了这个熟悉的冰冷瓶子,全副武装后,我打开了外面的灯。从侧面的小窗望向门廊,地上的雪嘎吱作响,被我称作“鬼怪”的邻居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裹着一件旧羊皮大衣,双手搭在臀部,我时常看见他在屋外劳作时穿着这件衣服。羊皮大衣里面露出穿着条纹睡裤的双腿和厚重的登山鞋。
“开门。”他说。
他惊奇地看了一眼我的亚麻布睡衣(这是去年夏天教授们本想要扔掉的料子,因为它勾起了我对旧时尚和青年时代的怀念,于是拿来当作睡衣。这被我称为实用主义与情感需求的结合),毫不客气地进了屋。
“快穿上衣服,大脚死了。”
那一瞬间我竟说不出话来,默默从衣架上随手拿了件羊毛外套,穿上高筒雪地靴。外边门廊上的雪在光晕中如梦般缓慢洒落。鬼怪静静地站在我身旁,高高的个头,纤细得瘦骨嶙峋,仿佛素描里勾勒的人物。他每移动一步,身上的雪就像酥皮点心上的糖霜一样飘落。
“什么叫‘死了’?”开门的同时嗓子里一紧,我终于还是开了口,鬼怪却没有回答。
他平时就沉默寡言。他的水星一定落在哪个沉默的星座上,应该是天蝎或是两宫交汇点,也有可能是土星的正对位,又或是水星逆行所产生的隐匿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
我们走出了门,熟悉、潮湿的冷空气迎面袭来,它似乎想在每年的冬天提醒我们,世界不是为人类所创造的,至少有半年时间对我们极不友好。严寒在野蛮地侵袭着我们的脸颊,嘴里吐着白汽。门廊上的灯自动熄灭了,我们摸黑在沙沙作响的雪地里前行,鬼怪的手电筒也指望不上,那电筒的光只能从他面前一片狭窄的区域内刺过黑暗,我跟在他身后踉跄前行。
“你没有手电筒吗?”他问。
我当然有,但是也要白天有光亮的时候才知道在哪儿啊。手电筒总是这样,只有白天才看得到。
大脚的小屋位置较偏僻,比其他房子要高出一些。他是这儿的三个常住居民之一。只有他、鬼怪和我三个不怕冷的常年居住在这儿。其他的住户一般十月份就把屋子封了,将水管里的水排空,回到城市里去。
我们从联通各家各户的主路上拐出来,路面上的雪显然有人扫过。延伸至大脚家的是雪地里一条被踩得极深的窄道,我们不得不一步一个脚印地,前后脚跟着,努力保持平衡。
“一会儿你看到的场景可能没那么令人愉悦。”鬼怪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道,电筒的光亮是如此刺眼。
我也没想过能看到什么愉悦的场景。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开了口,好像想解释些什么: “他厨房里的灯和母狗哀怨的嚎叫使我不安。你什么都没听到吗?”
不,我什么都没听到。我睡了,在酒花茶和安定的作用下睡得很沉。
“现在在哪儿,那只母狗?”
“我把它带回自己家了,给它喂了点吃的,现在它安静下来了。”
又是片刻沉默。
“为了省电,大脚总是早早的就关灯去睡了。今天灯却一直这样亮着,一直。雪地上有白色的线条。透过我卧室的窗子能够看到。我想他是不是喝醉了,或是又对他的狗做了什么,以至于它如此嚎叫。”
我们穿过摇摇欲坠的牛棚,两双闪烁的眼眸穿过黑暗映入鬼怪电筒的光,那是苍茫的绿色和荧光色的眼睛。
“看,是鹿,”我提高了嗓门,抓住鬼怪大衣的袖子,“它们离房子这么近,难道不害怕吗?”
鹿站在雪地里,雪已经没过了它们的肚子。它们平静地看着我们,就好像是在执行某个仪式时被我们逮到了一样,那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仪式。天很黑,我无法判断它们是秋天从捷克来的那些“年轻女士”,还是新的来客。而且为什么只有两只?那时候来的至少有四只。
“回家去。”我冲小鹿挥了挥手。它们抖了一下身子,却没有挪动,而是平静地目送我们一直到前门。我感到背脊一阵颤抖得发凉。
而鬼怪此时正跺着脚,在这座无人打理的屋前抖落鞋子上的雪。屋子的小窗用塑料和纸板密封着,木门上贴着黑色的胶油纸。
大厅的墙壁上堆着不平整的柴火,屋内肮脏、杂乱,四处弥漫着潮湿木头和泥土的味道,湿润而贪婪。陈年的烟味已在墙壁上结成了一层油腻的沉淀。
厨房的门半开着,我一眼便看到大脚躺在地上。就在目光即将落在他身体上的那一刹那,我移开了双眼。片刻后,我才敢于回过头来直视。那是十分可怕的景象。
他躺在地上,身体扭曲。手架在脖子上,好像在挣扎着试图解开束缚他的衣领。我像是被催眠了一般,不由自主地慢慢靠近。我看到他睁着的双眼似乎盯着桌子下方的某个地方。他那肮脏的衣服在靠近喉咙的部位被撕裂。好似自我搏斗了一番,z后又败给了自己。
恐惧让我感到寒冷。血液在我的血管中冻结,流入了身体的z深处。要知道昨天我看到的还是一个鲜活的躯体。
“我的上帝,”我急促不清地说,“发生了什么事?”
鬼怪耸了耸肩。
“我的手机在这儿无法报警,收到的是捷克的信号。”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电话号码——997。不一会儿我的手机里传来捷克移动服务的语音自动回复。运营商不断切换的现象有时在我的厨房里长时间存在。在鬼怪的家或者露台上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它的反复无常很难预测。
“得走到屋外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去。”我的建议显然已经迟了。
温馨提示:请使用德清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一位杰出的作家。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斯韦特兰娜·A·阿列克谢耶维奇
一个曲折的、充满想象力的、超越类型化的故事。(《糜骨之壤》)既是犯罪悬疑小说,又是童话,更是一场关于一些物种为什么要凌驾于另一些物种之上的哲学探讨。
——《时代》杂志
托卡尔丘克是过去25年间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家之一。
——《经济学人》杂志
托卡尔丘克是欧洲z受喜爱的和z独特的作家之一,她惊人的文字表现力体现了她在文学思想方面勇敢且成功的尝试。
——《洛杉矶书评》
一个不可思议的、寓言般的怪异的神秘故事……托卡尔丘克是掌控节奏和悬念的大师,它向人类行为投去锐利的目光。这不仅仅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更像是一部哲理童话,它试图抖落关于生与死的全部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保持敏感和警觉,把你的耳朵贴在地上,你将彻底明白一切。
——《纽约时报书评》
尽管采用了侦破谋杀案的线性结构,但(《糜骨之壤》)令人毛骨悚人的幽默感,以及是不是插入的怪异的哲思,是独属于作者的风格。托卡尔丘克是一位极有天赋和原创性的作家。
——《华尔街日报》
一部出色的,神秘的,深具文学性的犯罪小说。
——《芝加哥论坛报》
《糜骨之壤》以一种尖锐且个人化的方式令人感到振奋,这几乎是无法言说的;在存在主义层面,这部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过这样的作品。
——《纽约客》
一曲给大自然的颂歌;一首给威廉·布莱克的赞美诗;托卡尔丘克是否超越了布莱克?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波兰可谓家喻户晓,她继承了欧洲的哲思文学和杂文类小说的传统,是欧洲z重要的一批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家之一。
——《卫报》
第一人称叙事开头的故事总是能鲜活地展现主人公的个性,你立刻就想把所有时间都投入阅读之中,《糜骨之壤》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它深具颠覆性,挑战着人类权力带来的自鸣得意。
——《波士顿环球报》
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小说——因为托卡尔丘克不是一位平常意义上的作家。借由她非凡的才华、智识和她的这些“思想小说”,她提出并思考着关于生态环境的政治的种种问题。托卡尔丘克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并呼吁我们采取行动。
——《赫芬顿邮报》
令人着迷的逆时代潮流之作,它探讨的主题包括从动物的权利,到预先决定性,到社会对于那些被认为疯狂、怪异,或仅仅是不同的人的羞辱和边缘化。托卡尔丘克有创造奇迹的能力。
——《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
杰作!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妙趣横生,鲜活生动,危险,又令人忐忑不安。这部作品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尖锐问题。
——作家 安妮·普鲁
《糜骨之壤》令人坐立不安但又透露着充满诡异的友善。这部作品具备着威廉·布莱克式的浪漫、占星学的知识和中欧风光的同时,既是对人类恻隐之心的的沉思,也是一个可以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谋杀之谜。
——作家 马塞尔·泰鲁
我深爱这种扭曲的、充满忧郁的哲学性的神秘感。这是一部引人入胜、不断地发人深省的作品,因为这种存在本身的怪诞性而耀眼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