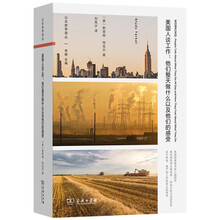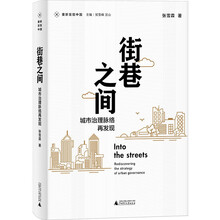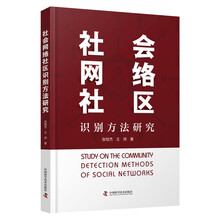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小说与城市间的密切关系很可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难理解,这种关系一直是长篇大论、有时又单调乏味的批评性讨论的主题。如果小说的读者和关注者一直以来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且如果小说这一于印刷机发明之后出现的唯一重要文体是出类拔萃的现代文学文体,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小说应当一而再、再而三地聚焦于城市这一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剧场及集体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在整个现代阶段经历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具动态的成长。
然而,大多数对于这一大论题的讨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集中于城市的物质现实是如何在小说中挂上号的。无论是在天真地、至少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文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老派批评家中,还是在新派批评家中(无论他们是马克思还是福柯的近代追随者,抑或是两者的追随者),这种集中性都同样明显。也就是说,新老阵营的批评家们都津津乐道于小说是如何“表现”或“反映”城市现实的。他们追问,从阅读有关伦敦的贫民窟、巴黎的下水道、19世纪大都会新兴的购物商场的时代小说中,从阅读有关股票市场、妓院、上流社会和剧场之类的机构的时代小说中,从阅读有关阶级关系、社会流动性、权力机制和城市生活的新经济压力的时代小说中,一个人能够了解到些什么?
当然,此类问题往往并非与许多小说家,特别是19世纪的小说家所想到的种种目的毫无关联,因为有些作家会把自己的行为想象为一种有关当代世界的特权独享的报告文学形式。但对物质现实和社会机制关注的表现往往模糊,小说写作与新闻写作之间还存在着质的差异,而且在从小说想象走向客观的集体现实之时,可能还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毕竟,写一本小说,就是从一个高度渲染过的视点来重塑这个世界——这一点不可避免,小说家们常常如此,包括小说中的人物。个人想象的这一艰辛过程既清晰地体现在诸如声称自己是当代社会小心翼翼的实验生的埃米尔·左拉这样的小说家身上,也体现在弗吉尼亚·伍尔芙这类抒情小说家身上。
在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直至20世纪初的这段时期(这正是本书以下章节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小说的一种决定性发展是这样一种实践:叙事越来越多地通过小说主人公或主人公们每时每刻的体验——感官的、感觉的、精神的——来进行。即使是在小说家同样时时刻刻地关注社会和物质的直观表现之时,这种我应当称之为实验现实主义的普遍程序也可以成为叙事的中心。实验现实主义的微妙展开与都市现实新秩序的出现问的交叉点,正是此处呈现的从福楼拜到卡夫卡和乔伊斯等一系列小说家所考虑的对象。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的前几十年,欧洲大城市呈指数级地发展壮大。(美国城市也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却较少成为小说家们的关注对象,因为其发展出现在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文化语境中,所以在此处的单一框架中尽量不同时讨论两者似乎是种审慎之举。)有大量证据(其中很多是文学之外的证据)表明,城市的这种迅猛增长引发了都市体验本质中的某种根本性变化。从建筑到公共交通再到经济,无论新的客观现实是什么,个人对生活在这种新都市地带的感受都迥然不同——步行在城市街道之上,融入市区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暴露于呈几何级增长的喧闹与杂乱之下,居住在城市新兴人口聚集区的公寓大楼或出租房屋里。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基本分类、自我的界定、个人自主权的感知开始发生变化。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