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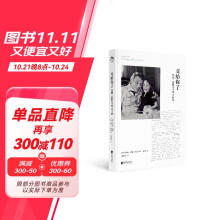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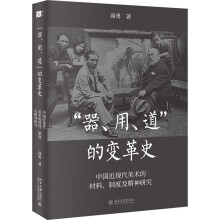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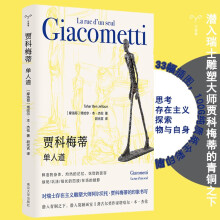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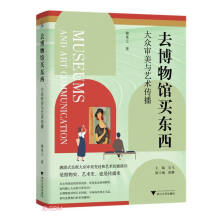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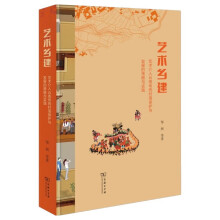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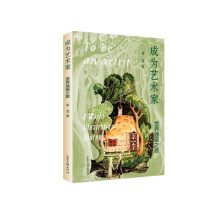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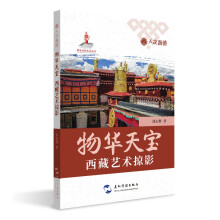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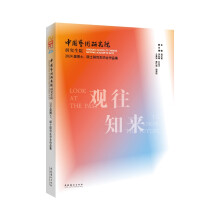
本书为著名美术史学者朱万章的全新力作,作者多年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观展与鉴定之余写下书札短评数篇,聚焦近百年来的书画家、学者、鉴藏家,通过对其往来书信的考释,将他们的“朋友圈”连点成线,并用独特的视角挖掘其间的私交趣事,小中见大,略窥百年来书画鉴藏与学术嬗变的印记。书中多数信件均为首次公开梓行,让我们在欣赏学人率性书法手稿的同时也能窥见人物性格的多面侧影。
大师的另一面(节选)
——黄宾虹信札中的齐白石
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视野中,黄宾虹和齐白石都是两座不可或缺的重镇。在黄宾虹与友朋往还的信札中,曾多次出现和齐白石相关的记录。透过散落于信札中的吉光片羽,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黄宾虹和齐白石的艺术传播情况与被社会接受状态,以及在当时艺术赞助人眼中的市场价位。
一
黄宾虹(1865—1955)和齐白石(1864—1957)都是二十世纪有名的书画家,两人年龄相若(齐比黄年长一岁),又同享高寿(黄九十一岁,齐九十四岁),又同时在一段时间寓居北平,且有过交集,有共同的朋友圈。
两人同在北平期间,有过若即若离的交游。据王中秀编著的《黄宾虹年谱》记载,黄、齐二人最早有过间接交集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12 月。其时,两人都有作品参加在上海文监师路日本俱乐部举行的“鼎脔同人书画展览会”,而彼时齐白石在北平,因而两人应无几率会晤。在1928 年6 月3 日,齐白石和黄宾虹等二十余人被jiao育部推举为全国美术展览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 年9 月,黄宾虹等人被推举为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鉴别委员,而齐白石有作品参选并入围。故在1928 或1929年或之后,两人或有机会见面相识,但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并无相关的明确记载。在此后的十余年间,黄宾虹和齐白石均有作品参加“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1929)、“巴黎中国画展”(1933)、“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1933)、“日内瓦中国画展”(1934)、“墨社第二届画展”(1937)、“京华美术学院成绩展览”(1940)、“雪庐画社时贤扇展”(1941)、“汪采白遗作展”(1942)、“大东亚美术展览会”(1942)、“齐白石、溥心畬先生画展”(1946)等展览,且两人还有共同的女弟子吴咏香。即便两人有如此多的可能的交集,但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直到1946 年止,均无两人会晤的准确记录。1944 年1 月11 日,北平艺专同人刘凌沧、邱石冥、赵梦珠、黄均等邀集在北京中山公园为黄宾虹祝寿即席挥毫,齐白石虽然没有到场,但在雅集画册补绘寿桃,题“华实三千年”。直到1946 年3 月12 日,北平“故都文物研究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成立大会,黄宾虹和齐白石等人受邀参与此会,并合影留念。这一年,黄宾虹和齐白石都已年过朝杖之年,在与会者中,两人都属年高德劭者,故在现存十二人的合影照里,两人均并列居中,这是目前所见两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中的最早文献记载。次年(即1947)11 月中旬,山东画家于希宁到北平举办个人画展,委托黄宾虹修函拜谒齐白石,齐白石亲临展场,并合影留念。

1946 年3 月12 日,故都文物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成立,右五
为齐白石,右六为黄宾虹,左五为溥心畬,左六为陈半丁。
在照片中,黄宾虹、齐白石两位最年长者,居于前排正中。 此外,1954 年4 月9 日,书法家王传恭在致函黄宾虹时说:“十五年前由俞瘦石、齐白石两世伯之介,得识公于石驸马后宅高斋,嗣又偕汪慎生兄晋谒数次,并承赐折箑,至今已几易沧桑,不知长者尚能忆及否?日昨至友徐忠仁兄奉命来杭迎驾北来主持中央民族艺术大计……首都友好、艺林学子翘首文旌,毋任鼚鼓。何日抵京,盼嘱忠仁电告,当赴站恭迓也。”按此时间倒推十五年,则至少在1939 年,是由齐白石等人引荐王传恭认识黄宾虹。可见,作为北平享有盛誉的黄宾虹、齐白石二老,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均相互引荐他人结识对方,说明两人在彼时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均成为后辈晚学争相寅缘的对象。

1947 年11 月15 日,于希宁画展在北平举行,前排左二起:于非闇、周养庵、齐白石、黄宾虹、陈半丁,右一为汪慎生;后排左四于希宁、左六王雪涛、左八李可染。
二
耐人寻味的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关于黄宾虹、齐白石两人公开交游的文字记录并不多,但在黄宾虹和友人往还信札中,则多次提及齐白石。这些早前仅限于两人之间具有私密性质的个人函件,如今已公开梓行,化身为公共资源,据此可从不同视角看出其时的齐白石与黄宾虹的关系,亦可从不同角度看出齐白石的艺术形象。
据不完全统计,黄宾虹往还信札中涉及齐白石的有九通,受信人有黄树滋、吴载和、汪聪、朱砚英和张虹,来信者有傅雷和张虹,时间集中在1946 年至1948 年。张虹是唯一一个往还信札都提及齐白石者,而黄树滋、朱砚英则是至少有两次信札涉及齐白石的受信人。故所有信札虽然有九通,实际涉及的往还信札者,除黄宾虹本人外共有六人。
涉及齐白石的往还信札,大抵可分为两类:一是谈及其书画润例,一是涉及对其绘画展览及评介。关于前者的信札较多,共七通;关于后者的信札仅有致朱砚英及傅雷来信各一通。
温馨提示:请使用常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黄宾虹在致黄树滋的信中两次谈到张大千的鬻画,一次这样写道:“张大千来此售画,每张定价法币二十万元,齐白石每尺方四万元,皆甚忙碌。鄙人只择人而与,非经知交介绍不动一笔,各纸铺索者皆谢绝之,意留传精作,不与人争名利耳。”1字里行间,似乎充溢着不屑。
另一通信札也透露出同样的情绪:“今年学徒之辈收润均加数倍(此间人取张大千每方尺订三五仟元之多,可笑),而鄙人近十余年来无润格,不欲与时贤争胜也。”2黄宾虹在2 月10 日致吴载和的信札中也提及张大千润格:“最好雅事不取金帛,第近来各物日增价值,殊为惊人。因此齐白石每方尺订法币四仟元,张大千每张十六万,与纸铺合同办理,为空前获利之举,鄙意不欲赞同之,仍守择人而予而已。”3 显然,黄宾虹对作为晚辈的张大千的过高定价是颇有微词的。
事实上,不仅在黄宾虹的信札中谈及张大千的价格高位,在当时的报纸中也有相关报道。同年10 月26 日,在北京由中山公园董事会举行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第二十届展览会,张大千有一幅《青城红叶》标价1200 万元,“令观众咋舌”4。时年不到半百的张大千在画艺上正如日中天,年轻气盛,故通过高定价来自抬身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彼时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就其单位价格看,确实很高,但如果和同一年的其他书画家相比,似乎就不是特别突出了。1947 年12 月27 日,《大公报》刊出书法家金梁的润格,对联四尺为壹佰万元,中堂四尺为贰佰万元,册卷每尺五十万元5,张大千与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其润例自然就不算高了。
当然,在这段时间,黄宾虹也并非如其所说“近十余年来无润格”,事实上,在1945 年他还拟定了“虹庐润例”:“堂幅屏幅每方尺二百元,扇面手卷册页按方尺计,设色双款加倍,题跋点格另议,润资先惠,立索不应”6(此处的定价当非法币),可见,带有私密性质的信札与面对公众的信息未必是统一的。黄宾虹在信札中对张大千、齐白石等人润格的态度,或许折射出此时已名满天下而润金却处于低谷的黄宾虹的巨大心理落差。
(选自《张大千的鬻画与推广——黄宾虹往还信札中的另类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