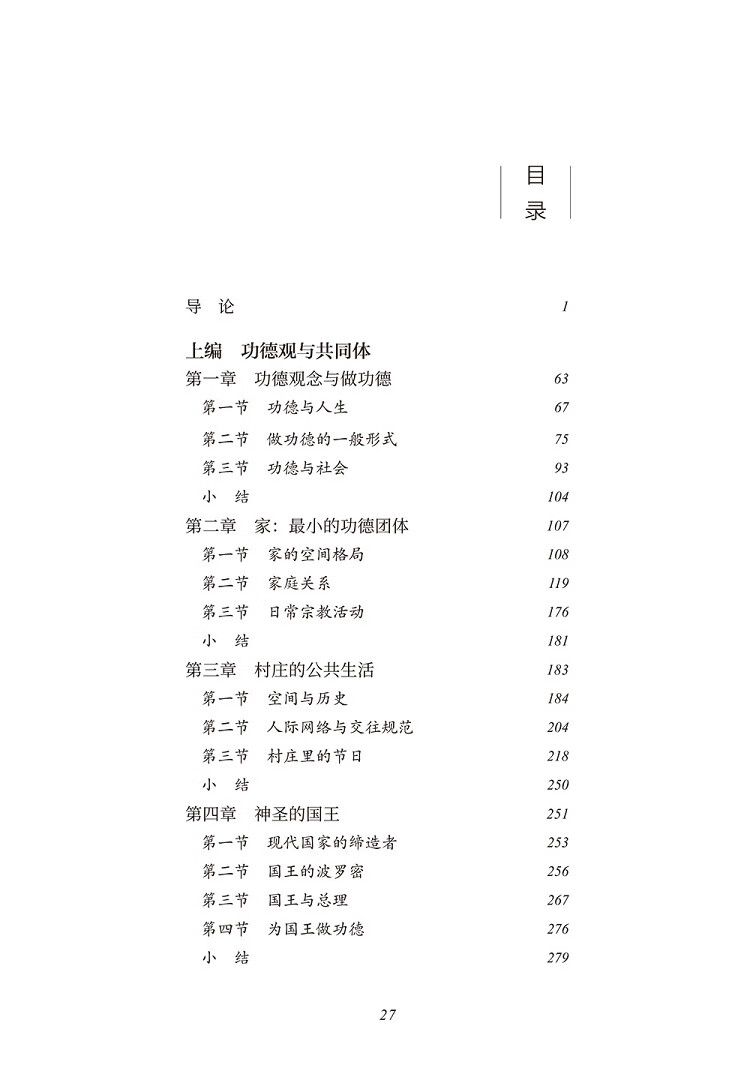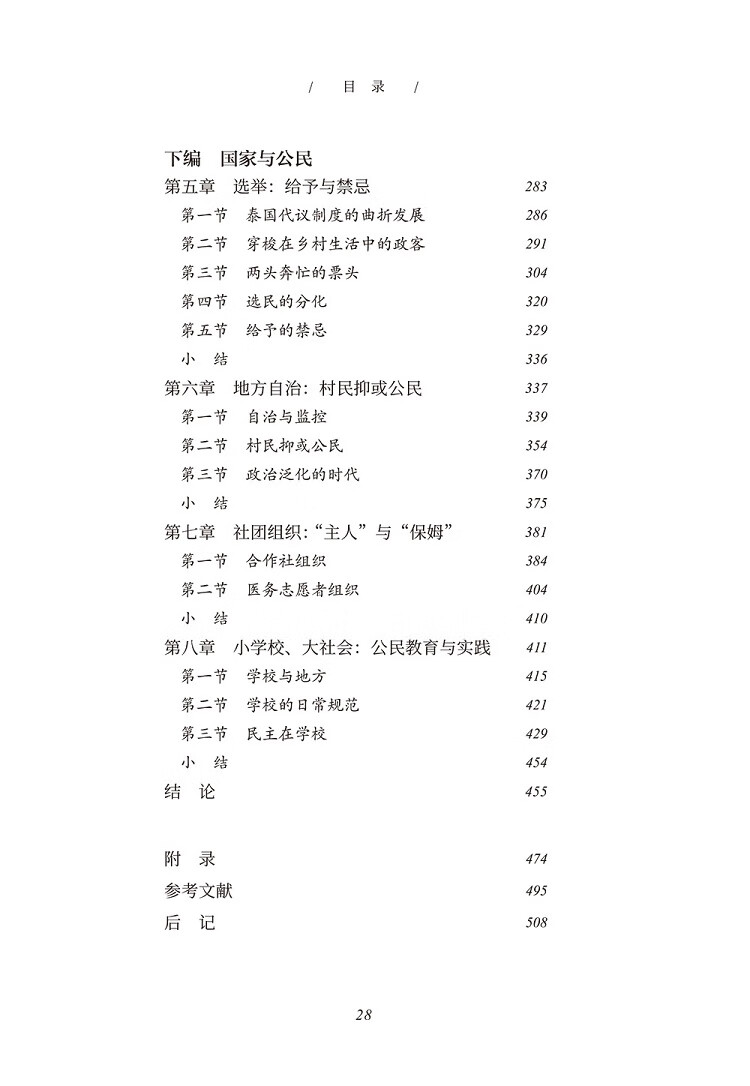导论
2003年2月9日14点,我在初春的寒意中登上从广州至曼谷的飞机, 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将要飞向自己的田野工作地点,开始一次独特 的人生之旅,心中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的心情也极为忐忑 不安,因为这不是轻松的旅行,而是一段充满了各种未知数、对我的人 生又将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无法重复的经历。当时,我的泰语才处于起步 阶段,交流上的困难不知如何才能克服;我在泰国的社会关系也十分有 限,我只联系了朱拉隆功大学的国际合作办,他们能否帮助我选择一个 合适的调查地点还不得而知。即使在进入田野之后,我是否能顺利开展 调查、调查将会发现什么、材料能有哪些价值也都是无法预期的。
如果说这是一段没有明了的路线和终点的旅程,那么起点就显得 格外重要,因为它首先确立了某种可能性。对于人类学学者而言,异域 田野的起点是对本土社会的关怀,而人类学的魅力正是在于异域与本土 的对立统一。正如德怀尔所说的:“人类学家个人的探索与他所来自的 社会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他 怎样赋予经验以形式,他如何形成和提出问题,他如何解释和得出答 案—都为那些利益提供了一个注释。”(Dweyer,1987:17)因此,期待着用自己在异国他乡的探索经历来回应对本土社会的思考成为了我作 为一个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信念。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探求的是一个总的问题,即现代化在中国如何可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变得更为复杂而非更为明朗。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新启蒙思潮曾一度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的合理目的,但是,90年代以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暴露了这一思潮的局限性。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和信任危机都动摇了人们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人们一方面呼唤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担社会失范带来的后果。那么,现代性有没有更理想的表现形态?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借鉴和启发呢?这是我从事海外民族志所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研究的理论切入点。从人的意义上说,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塑造现代公民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实现资源的合理再分配的经济问题,也不仅是如何让社会成员参与民主管理的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创造出与民族国家一体的象征符号并带来成员之间的交流、共识与认同的文化问题。就中国而言,现代化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我们盲目地抛弃传统的文化资源,我们的国家迫使公民脱离原来的“文化网络”去直面赤裸裸的现代国家的权力(杜赞奇,1994[1988])a;结果,在对历史传统的自我否定之后,我们却发现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和意义表达是那么贫乏。那么在泰国,“做一个公民”对人们意味着什么?他们怎样看待国家与公民、传统与现代化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呢?他们的困惑又是什么呢?
带着以上这些问题,紧张、不安又充满好奇心与探知欲的我在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于当地时间15点30分抵达了曼谷。当我走出廊曼机场时,一阵热气迎面扑来。当天的最高气温是33℃,空气湿度非常大,我感觉喘不过气。
曼谷是一个喧闹躁动的城市。它的街道两旁楼房密集,道路十分拥挤。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当地的交通非常糟糕,堵车是家常便饭。据说在某一年的宋干节期间,曼谷的主要道路曾创下堵塞48小时的纪录。同时,曼谷也是相当国际化的。到达曼谷的最初几天,我似乎还没有感受到进入异文化时所产生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这个都市更多地让人想到全球化的概念。在商场,人头攒动的顾客中至少有1/4是西方游客;电视里居然播放着泰语版的台湾连续剧《流星花园》并让不少年轻人着迷;充斥着各种国际品牌商品的花花世界鼓动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当我操着不熟练的泰语与大学里的工作人员、路人或售货员对话时,他们立刻开始用英语和我交流。
但是,曼谷也不时表露出冷静执着的底蕴。当地人丝毫不苟地坚持本土的时空框架和行为规范,这种坚持在我看来带有真正的性格。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