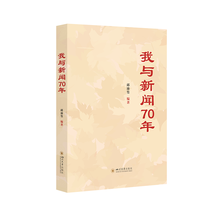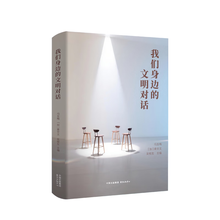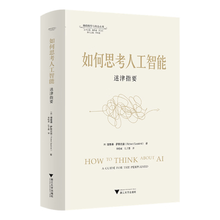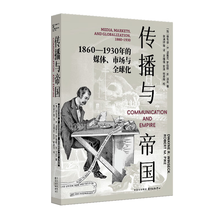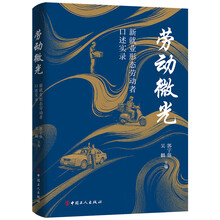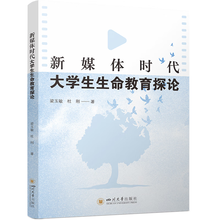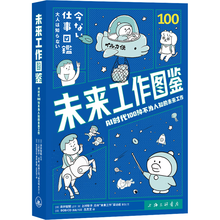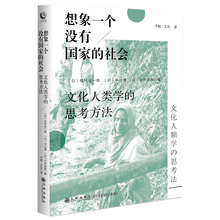社会科学研究为何要走入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以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存在不同的研究旨趣为前提。社会科学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学术界,是知识学科化和专门化发展的产物。实际上,历史学最初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一起,也被纳入社会科学的范畴。但两者由于旨趣的差异而渐行渐远。这种差异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在研究目标上,社会科学追求发现制约人类行为的普遍性法则,历史学则追求还原历史事实;二是在研究对象上,社会科学出于分析的需要而认为有必要将人类现实分成不同部类,历史学则反对这种分割,强调历史过程的整体性;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强调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包括以理论为基础提出假设、严格的定量程序等,历史学则偏重于文献和档案研究,计量史学即使在今天仍然地位尴尬;四是在研究资料上,社会科学偏爱通过系统方法来获得证据(如调查数据)和通过受控观察获得资料,不大喜欢普通文献及其他残剩资料,历史学则对后者情有独钟。 不可否认,社会科学在其最初发展阶段更受当时一日千里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思维在研究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以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实证研究则是这种追求的早期典范。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分野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社会学家乐于把时间上的演进留给历史学家来研究,而作为交易的另一方,历史学家则把社会体系的结构性特征留给社会学家。” 然而,社会科学研究纯粹“科学”的追求很快被证明并不可行,这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使然。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本身,社会则由“人”构成,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仅具有能动性和价值性,而且以之为基础的社会也具有历史延续性,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是对当下进行“横截面”或“拍快照”式的研究。社会无法切断与历史的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也无法不顾及历史的存在。在把历史带入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以韦伯(Max Weber)等为代表的经典思想家率先做出示范。韦伯不仅将价值、文化因素带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强调历史阐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对个人的社会条件及其持续存在的原因进行经验—心理的分析或历史的分析,除了进行‘理解’式的解释(understanding explanation)外,不会有任何收获。这一点丝毫不可以忽视。”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其从历史文化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做出解释的典范。到了20世纪中期,“历史”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西方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以历史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等的制度化(学术团体、期刊、课程、职业市场)作为标志,历史正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根据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的观点,西方历史社会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T. H. 马歇尔(Thomas Humphrey Marshall)、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塞缪尔·艾森斯塔德(Samuel Eisenstadt)和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等思想家为代表,所针对的主要是极权主义;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为代表,所针对的是当时此起彼伏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存在时间重叠,从20世纪70年代末延伸到90年代,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安东尼·吉登斯等为代表,所针对的主要是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 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不是要使自身变成历史研究,而是要借助历史的意识和资源来实现对重大社会变迁的理解。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是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的重要标志。丹尼斯·史密斯指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索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 著名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 Rahman)认为,历史社会学研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区分无关紧要的人类日常活动与改变社会结构的罕见时刻;二是解释具有变革性的事件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而并非发生在别时他处的原因;三是揭示一个事件如何引发其后事件。 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凭借历史来理解当代社会中具有非凡意义和影响深远影响的那些内容。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是立场方面的,认为社会变迁具有延续性,需要将当前社会置于历史和结构的视野下加以考察;第二个是方法论方面的,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学方法的创造性改造来满足自身的解释要求;第三个是目标方面的,历史解释服务于理论建构的目标,即通过提炼历史进程中的规律性要素来获得对于社会变迁的理论认识。历史学侧重于对历史本身的理解,个案延展通常遭到抵制;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共性的重要程度高于个性,社会科学研究试图通过对历史个案的解释来创建理论,从而解释更多的个案以及、解释共性与个性的各自成因。 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是以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作为基础的。为理解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吉登斯在“历史”(histor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进行了区分:前者表示“时间流逝之中事件的发生;对这些事件的编年记载或解释说明” ;后者则表示“利用过去来帮助构筑现在……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 。从时间观念上来看,历史表示人类在时间流逝中的“度过”,过去的时间支配和主宰着当下与未来,体现在传统、宗教等的支配上;历史性则表明当下和未来支配过去,过去仅仅是帮助构建现在和未来的资源。前者反映了前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后者则反映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并且本质上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种现象。社会科学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伴生物,从源头上讲,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也是“历史性”的体现。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立场并不是把历史当作任人编织的发辫,对于历史事实的尊重是走入历史的基本要求。或者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就是要在长周期、扎实史料的基础上理解社会发展规律,这是唯物史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要求和体现。 至此,我们可以对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的原因做出总结:社会科学研究走入历史以两者所具有的不同学术旨趣作为基础,社会科学旨在通过汲取历史学的方法、视野和史实来补齐自身的短板。走入历史不是要使社会科学变成历史学,而是为了使社会科学更好地服务现实和未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