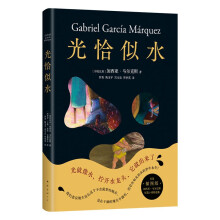车停在沙逊房子前面,各色各样的人挤进来了。一个面目黎黑的外国人来坐在她旁边,把她一直挤紧在角落里。但是这外国人没有坐定,就立起来让给一个很美丽的,穿着一件网纹绒线衫的外国女人了。她这一旁的座位上,除了她,差不多全给外国女人占据去。这些都是大公司里的女职员。好福气啊,她们身体这样好,耐得了整天的辛苦。可是,难道她们都没有孩子的吗?
车还没有开动。卖报人不但嘈杂地高叫着,并且还把报纸从车窗里乱塞进来,擦着每一个乘客底肩背或脸。她回过头去,一张报纸晃动在她眼睛前,一个沙嗄的声音:‘刚刚出版格号外时报。’她摇摇头。一个老枪闪了过去。扶梯底下的报纸该卖掉了,已经堆不下了。这几个月的报纸真冤枉,简直都没有看。最好能够单定一张本埠增刊,翻翻戏报就够了。………不过,也难,大廉价的广告又都登在第一张。………看广告常常容易上当,多花费,今天早上要是不看见这医生的大广告,这一趟也就省掉了。呃,明天准定叫阿蓉回了。………再不然,就定一份便宜点的,横竖有大事情的时候好再定。
卓佩珊夫人正在打算节省一点报费的时候,一个锐利的孩子声突然在她耳朵边嚷着:
——阿要看,今朝夜里,扫帚星出现!
扫帚星,她记得好久没听到过这名字了。她没有看见过这颗星,但是她晓得这不是颗好星宿,因为她小时候,妈妈宠了她,嫂嫂就在厨房里说她的背话,骂她扫帚星了。
——难得看见,三十三年一转!
嘹喨的叫嚷又在她耳朵边响着,于是站在她前面的那个围着白丝巾的男子,从她肩膀上伸出一双手去,以两个铜元换来了一张报纸。
车开动了。她才注意到有许多人买了报纸。时报,大晚报,新夜报,还有英文的晚报。这些人是不是都预备看扫帚星的?这是不是像月蚀一样的东西?是一颗很大的像扫帚一样星呢,还是许多星排成一柄扫帚的样儿?今天晚上,人家会不会敲锣放炮呢,像前年月蚀的时候那样?她这样怀疑着。
她耐心地等待着前面的那个男子把报纸翻过来,当他看别的新闻纪事的时候,她可以偷瞧见关于扫帚星的新闻。究竟怎么说着?可是车好像已行过了两三站路,他还没有看完一版新闻。太慢了!这个人真够笨,看这样一张报还得费这许多时候。她顺眼看别的人,有的正在翻看后幅的新闻,有的已经看完了,把报纸折起来塞在衣袋里。她开始后悔刚才不自己买一张。但是,女人在车上买报纸看,这倒好像是稀有的事,她似乎并没有看见过先例。
于是车停在永安公司门前了。他才移动了手中的报纸,但并不翻过后幅来,他把报纸忽急地折拢来,挟在腋下,回头一望,在人群中一阵子乱挤,下车去了。她觉得好像被侮辱了,有些不便出声的骂人话从她心里涌上来。各种各样的晚报的叫卖声,依然在她耳朵里响着:
——要看豪燥,大晚报,号外时报!
但她没有从手皮包里取出铜元来的勇气。车中人愈挤得多,旁边的那个穿网纹绒线衫的外国女人不住的挨过来。前面立着一个看上去很整洁的年青人——其实这男子和她是年纪相仿的,可是她并不以为如此,她以为他是一个美丽的年轻人。他给旁边和后面的人,随着车身的簸动而推挤着,使他底腿屡次贴上了她底膝盖。为了要维持他底礼貌,虽然她并不闪避她底膝盖能闪避到那里去呢?他不得不以一只手支撑着车窗上的横木,努力抵御着旁边人的推挤。她看得出他是很累的,因为他蹙着眉头,两个脸颊涨得通红了。她想对他说,不必这样地讲规矩,即使他底腿稍微
——不,甚至是完全,那也有什么关系呢?——贴上了她底腿和膝盖,她也原谅他的。但是,她真的可以这样说吗?
于是她想起了丈夫,身体一胖连礼貌也没有了。为什么他这样地粗鲁呢,全不懂得怎样体贴人家?她一件一件地回想,一直想到昨天晚上他吃牛排时候的那种蠢态。她曾开玩笑似地骂他一声‘猪猡’,可是他也不恼,只晃着脑袋笑,活像那个!天下的人真有那样的!也许,这又得想回头了,也许这些全是假的?也许他算是赔小心眼儿给我?要不然,难道他在行里做主任,也就是那样一副傻气吗?不会的,不会的,他不是傻子!
可是,为什么要假装着这样?我并不欢喜。我要他严肃一点,文雅一点。是的,文雅得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卓佩珊夫人抬起头来,这文雅的年轻人正在用文雅的眼睛注视着她底鬈曲的美发。在这样凝静的注视中,她看得出充满了悦意和惊异。她不禁伸手去拂掠这新近电烫过的青丝。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