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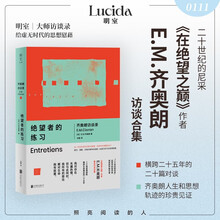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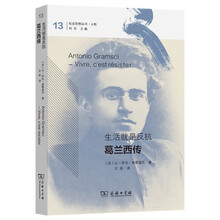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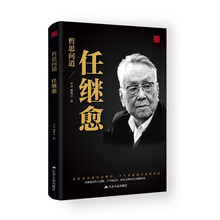




本书主要讲述了著名过程哲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对自己人生的追忆,反映了过去六十年来的宗教理论发展历程。从存在主义到过程哲学,从女权主义、黑人解放神学到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及“上帝之死”,作者在这些反思中充分贯彻了一个信念:学术研究必须联系实际问题。字里行间也透视了一位哲人居安思危、心系天下的情怀。
虽然神学回忆不必驻足于人的童年,但在另方面(至少我的情况是如此),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和使命却植根于童年。我童年之所思、之所喜,与我现在之所信、之所喜,这二者间是有持续性的。那可能意味着,我一直未对童年的信仰抱有足够的批判。我可能仍过分地坚持该信仰中在我看来仍有价值的那些方面。该信仰可能在过多的程度上仍在塑造我的见解和希望。不管那可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从小就被反复灌输的原则之一,就是诚实。所以,我必须说明,我自何来,我早年的成长经历如何现在仍在影响我。我还要承认,正因为当初在父母的影响下接受的信仰,我现在仍对他们怀着感激之情。
那么,那一信仰是什么呢?我的父母是监理公会的传教士。他们本期望到中国去,但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却被派往了日本。他们在那儿一直(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待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于1925年出生在那里,是我父母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姐弟三人都出生在帕尔默尔学院那个小小校园里的一幢日本风格的房子里。该学院主要是一个夜校,是为想学英语的日本人开办的。第二年,全家搬到广岛。此后我一直住在那儿,直到1931年和1932年间第一次回到美国。
我对在广岛生活的记忆非常有限。我4岁时几乎死于猩红热。我记得医生告诉我母亲说,倘若我不学会咕噜咕噜地含漱,则必死无疑。我显然的确是学会了。当然,我被隔离起来,尤其是与兄弟姐妹们隔离开来。但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大人们不准我家的狗进我的房间来。另一个深刻记忆则是,我曾与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进行过一次赛跑,我被远远地丢在后面。我一直喜欢把我的缓慢归罪于猩红热,且这一直是我为自己体育不行所找的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
再一个记忆是关于绯村的,那个小伙子几乎可算我家的人。我至今还记得,我如何从户外的楼梯爬进楼上他的房间。后来我作为占领军的一员回到日本,最新见得就是他。但他已战死于缅甸,天皇宣布投降后不久他还继续战斗。
直到1940年12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那时已战云密布,我的父母只好送我回佐治亚州去完成我的中学学业。第二年春天,他们也回来了。因为美国国外传教理事会认为,如果战争爆发,美国的传教士可能会成为日本教会的沉重负担。
一般来说,我的父母在宗教上是保守的。然而那时,作为一个保守的卫斯理宗教徒,甚至一个监理会教徒,也迥异于今日所称的宗教权利那样的东西。卫斯理宗的保守主义当时表现为极度的虔诚。同卫斯理一样,教徒注重的是规范自己的生活,以便尽量行善,以便在献身上帝和人类的过程中,内心尽量地保持纯洁。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那些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温馨提示:请使用常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