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4年《哈里森法》颁布以来,美国毒品控制之法律惩戒模式历经三个时段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模式无论在内容还是普及程度上,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了明显不同的气象。
如同本书第一篇美国禁毒外交内容所涉及的,美国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杠杆”作用一跃登上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之后凭借着强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在外交的各个领域里扩展并巩固着影响力。与此相对应,在禁毒外交的舞台上,美国也攫取了前所未有的强势话语权。由于立场不同与利益不一,在任何时候,国际毒品控制舞台都不乏各色“嘈杂”之音。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力量对比上的悬殊,足以让美国肆意驰骋,去深入参与所有国际毒品控制机构的组织工作,酝酿并参与制定每一个国际毒品控制条约。正因如此,美国也牢牢控制着并且深深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毒品控制的舞台,让美国所提倡的以禁止主义为核心的毒品控制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宣扬与实施。
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续,很大程度上也是内政的反映和需要。尤其就美国禁毒外交而言,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将内外两个方面的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联邦层面上来看,美国禁毒外交的发端早于联邦禁毒法的确立。美国第一部联邦综合性毒品控制法——1914年《哈里森法》,正是在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与1912年的“海牙国际鸦片会议”的有力推动下而订立的。反之,美国国内禁毒法内容的不断充实与扩展,也不断强化着美国在实施禁毒外交政策过程中传统傲慢、自以为是的“敌在外而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
这一禁毒领域“与生俱来”的内政与外交相互交叉影响的特点,在至今长达百年的美国禁毒外交史上,基本上以一种“内政即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的典型形式存在并持续至今。
在美国禁毒外交的影响下,法律惩戒模式得以建立并逐渐扩大其控制的范围。法律惩戒的核心内容,就是将传统的鸦片、大麻、古柯叶及其衍生物在非医学与科研之外的使用视为非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成瘾视为“罪恶”而加以禁止与惩戒。与此同期共存的禁毒理念是,美国毒品泛滥的主要成因源自外来因素,正是外来的麻醉品才导致了美国国内毒品问题的日益严重,故而断绝源产地毒品并杜绝其流入美国国境,就成为美国禁毒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自《哈里森法》颁布并实施以来,美国国内禁毒法往往成为禁毒外交的一个“道德与理论阵地”,借此不断在国际毒品控制舞台上,要求他国实施美国国内法的禁毒理念。在早期的国际鸦片会议上,一旦美国的这种要求同以鸦片贸易为一大经济来源的欧洲老牌殖民国家交锋之时,美国则时常备受阻力而陷入孤立的状态之中。这样充满沮丧的必然结果,既是当时美国实力的欠缺使然,也是美国与诸多欧洲国家的毒品控制理念间存在的差距所致。此外,这还是美国法律惩戒模式与禁毒外交之间的密切联系之真实写照。
考察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尤其是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美国法律惩戒模式的历史演变,除了关注美国禁毒外交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外,其他一些或直接或间接的内在因素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人文环境的变化对法律惩戒模式内容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发生了诸多与政治气候、人文环境以及民权运动相关的事件,尤其是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与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无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毒品控制之法律惩戒模式内容的变化。其次,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内禁毒政策并非是铜墙铁壁、牢不可破的。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美国国内针对成瘾是“罪恶”还是“疾病”这一问题的讨论渐次扩大并不断升级,其固有的僵化古板的禁毒模式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松动。特别是,在安斯林格退休后出现的毒品控制机构的人事变动,以及政党交替所导致的政策执行力度上的变化,同时对“古典时期”以来确立的法律惩戒模式产生了瓦解性的冲击。而之后的尼克松时代发起的“毒品战争”,在大幅实施国外截源的禁毒外交活动及加强国内的综合执法能力之外,在联邦立法层面上确立成瘾治疗模式,则无疑是美国毒品控制模式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出现的必然结果。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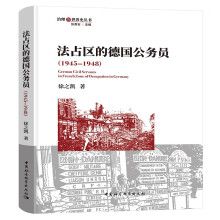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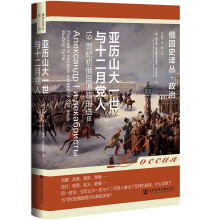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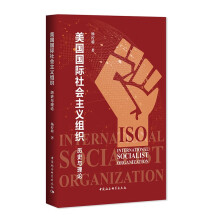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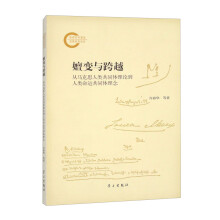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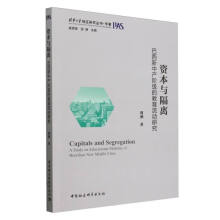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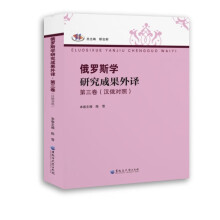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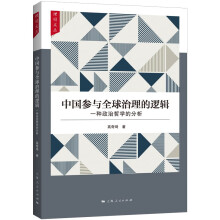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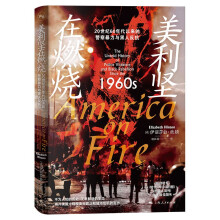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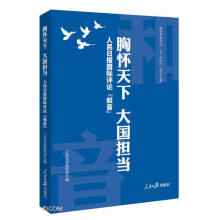
——美国禁毒史学者约翰·伽利赫(John F. Galliher)
联邦麻醉品法与毒品战争: 一个吃钱的无底洞。
——美国禁毒史学者托马斯·罗(Thomas C. Rowe)
即使在20世纪结束之际,在国际社会中,毒品问题依然呈现一种极为荒谬的现状: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已经摆脱了毒品滥用之威胁。
——国际毒品控制史学者威廉姆·麦克阿里斯特(William B. McAll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