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普代克作品:兔子,跑吧》:
一根电话线杆上固定着一块木板,有一群男孩正围在这儿打篮球。他们跑着,叫着,“克兹”牌球鞋踩得小巷地面上的松散碎石“吱吱”作响,仿佛将孩子们的叫声高高弹起,越过电话线,抛上那潮湿的三月的蓝天。兔子安斯特朗西装革履地走进小巷,他虽然已经二十六岁,而且身高六英尺三①,却止步观战起来。他身材太高,似乎与兔子的形象相去甚远,但那宽大的白脸,浅蓝色的瞳仁,以及将烟叼进嘴里时短鼻子下的神经质颤动,多少解释了这个绰号的由来——这是在他也还是个孩子时叫开的。他站在那里,心里想,小家伙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世上,真是挤得你够戗。
他就那样站在一旁,这帮真正的孩子不禁有些纳闷,不时地瞥他一眼。他们打球只是自娱自乐,可不是打给哪个穿着双排扣褐色西服满镇闲逛的大人看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大人竟然走进这条小巷,未免有些滑稽。他的车在哪儿?他嘴里叼着烟,更给人一种不怀好意的感觉。难道他就是那种掏出烟或钱,要他们跟他到制冰厂后面去的人吗?他们听说过这种事,可并不怎么害怕,自己这边有六个人呢,而他只有一个。
球从篮框上弹下来,越过六个孩子的头顶,落在兔子的脚边。就在球反弹而起的一刹那,兔子顺手接住,其动作之快令他们暗暗吃惊。他们一声不吭地看着,而他则透过蓝色的烟雾,眯起眼睛瞄着篮框,在春日午后的天空下,这突然出现的黑色身形犹如一尊烟囱。他小心地站稳身子,有些紧张地在胸前摆弄着球,一只白皙的大手五指张开贴在球上方,另一只手将球托着。他不慌不忙地晃了晃球,体会着其中的感觉。他指甲上的甲晕很大。接着,他双膝微屈,球似乎是从他右侧的衣领旁弹出,离肩而去。乍看之下,这一球好像不会投中,因为尽管他选取了一定的角度,球却没有向篮板飞去。它本来就不是瞄准篮板。它掉进了篮框,将篮网抽得“刷刷”直响,像女人的低语一般。“嘿!”②他得意地叫道。
“运气罢了,”一个男孩说。
“是技术,”他说,接着又问,“嘿,算我一个,好吗?”
孩子们没有回答,只是交换着困惑不解的眼神。兔子脱下西服的上装,整齐地叠好,然后放在一只干净的垃圾筒盖上。在他身后,那群穿工装裤的小家伙重新开战了。他走进混战中心去抢球,轻轻一拨,就把球从一个小家伙力道不足的脏手中打掉,接在自己手中。一接触到那熟悉的绷紧的皮革,他不由得全身紧绷,手臂也轻盈自如起来。这种全身紧绷的感觉仿佛又将他带回到了多年以前。他双臂轻松地一扬,篮球便从他的头顶向篮框飘然飞去。这准是一记漂亮的好球,可结果却连篮框都没有碰上;他眨了眨眼,一时还当是连篮网都没有接触的空心球呢。“嘿,我跟谁一边?”他问。
在不声不响之中,两个孩子被推了出来,成为他的队友,他们以三对四。尽管兔子一开始就主动让步,站在离篮框十英尺之外的地方,但这仍然有失公平。大家都懒得记分。这种不友好的沉默使他有些沮丧。小家伙们彼此只言片语地打着招呼,对他却不敢说一个字。打了一会儿之后,他感觉到腿边的小家伙们渐渐较劲了,想将他绊倒,尽管他们对他仍然一言不发。他可不需要这种尊重,他想告诉他们,长成大人也算不了什么,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十分钟之后,一个男孩转到另一边去了,于是只剩下兔子安斯特朗和另一个孩子以二对五。这小家伙是六个孩子中打得最棒的,虽然身材瘦小,但四肢灵活,羞怯中已显出几分自如。他戴着一顶饰有绿色绒球的编织帽,两只耳朵罩得严严实实,眉毛也几乎遮住了,显出一副憨头憨脑的样子。他是个天生的好手,根本不用迈步就能向旁边移动,滑行的姿势非常优美,从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还有他移动前停在那儿的准备动作。如果运气好的话,到中学时,他准能成为一名顶呱呱的运动员,兔子了解这种经历。你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最后到达顶峰,大家都为你喝彩;你眉毛上挂着汗珠,视线有些模糊,可四周一片欢腾,让你感觉飘然上升。然后,你退场了,起初还没有被人遗忘,只是退场而已,这让你觉得满足、舒爽、自在。你退场了,像冰雪融化一般,但依然在冉冉上升,最后变成这帮孩子眼中的又一小片天空,变成由镇里的大人所组成的笼罩着他们的天空中的一部分,突然莫名其妙地罩在他们头上,来造访他们。他们并没有将他遗忘,而只是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他,这比遗忘更令人难堪。而想当年,兔子在全县可是鼎鼎有名,高二那年,他创造了乙级篮球联赛的得分纪录,高三时又刷新了纪录,这个纪录直到四年之后——也就是离现在四年以前——才被打破。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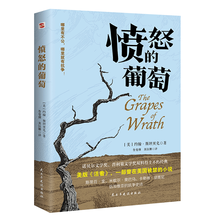








——《华盛顿邮报》
★“精准、优雅、震撼,厄普代克真是位语言和形象的大师,同时又是思想和情感完美的洞悉者。”
——《乡村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