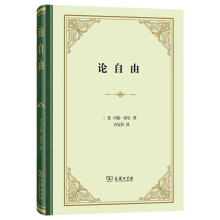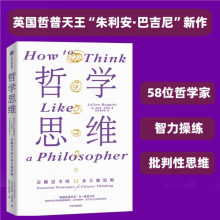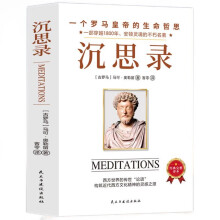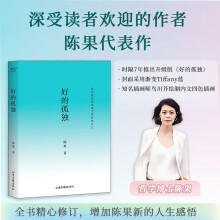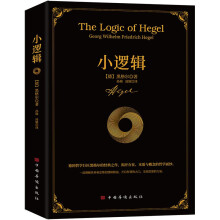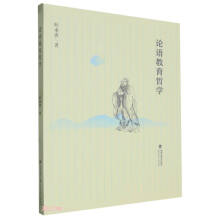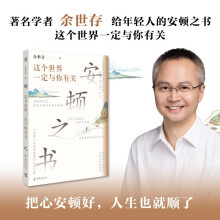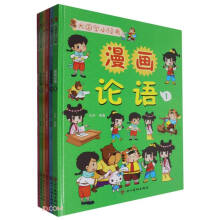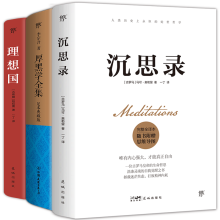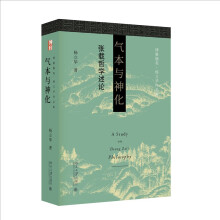《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理解性的与灵心善感的作品,就其对象也包含有某些感觉的东西在内而言,同样也具有上述区别的某些部分。对于宇宙之无穷大的数学概念、对永恒性的形而上学的考察、天意,我们的灵魂不朽,都包含着有某种崇高性和价值。反之,有关世界的智慧却也被许多钻牛角尖的空谈给歪曲了,而且貌似深奥却也并未能防止人们把四种三段论式说成是经院哲学的怪诞。③
在道德品质上,唯有真正的德行才是崇高的。然而也有某些善良的内心品质是可爱的和美好的,并且就它们与德行是和谐一致的而论,也应该看作是高贵的,尽管它们确切说来并不能够说就是属于道德性的心性的。有关这一点的判断,是微妙而复杂的。确实,我们不能称那种心情就是有德的,它只是那些行为的一个来源,——那些行为的确也出自德行,但其基础却只是以偶然的方式而与德行相一致,而就其本性来说却往往是与德行的普遍规律相抵触的。某些温情好意——那是很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同情感的——乃是美好可爱的;因为它表明了对别人命运的善意的同情,而德行的原则也同样地会引导到那里。不过这种善良的情感同时却是软弱的,而且总是盲目的。因为假设这种感情在推动着你,要你花钱去帮助一个困苦的人,而你又欠了另一个人的债,这样就把你置于一种无法严格履行正义的义务的地位了。所以,这种行为就显然不可能是出自任何德行方面的意图,因为这样一种情况不可能诱导你为了这一盲目的幻念而去牺牲一种更高的责任。反之,当对全人类的普遍的友善成为了你的原则,而你又总是以自己的行为遵从着它的话,那时候,对困苦者的爱始终都存在着,可是它却是被置于对自己的全盘义务的真正关系这一更高的立场之上的。普遍的友善乃是同情别人不幸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正义的基础。正是根据它的教诫,你就必须放弃现在的这一行为。一旦这种感觉上升到它所应有的普遍性,那么它就是崇高的,但也是更冷酷的。因为要我们的胸中对每一个人的遭遇都充满着温情,对别人的每一桩困苦都激荡着沉痛,这是不可能的事;否则的话,一个有德的人就会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不断地沉浸在伤感的眼泪之中了,尽管他有着这一切好心肠,却无非是成了一个感伤的、无所作为的人而已。
第二种善良的感情——它确实也是美好的而又可爱的,但仍然不是一种真正的德行基础,——就是殷勤;这种愿望是要以友好、以同意别人的要求并以我们的行为与别人的意愿相一致去使得别人高兴。这种迷人的社会性的基础是美好的,这样一种心肠的温柔性也是好意的。然而它却根本就不是德行。凡是在更高的原则并没有为它设定界限并削弱它的地方,一切罪恶就都可能从其中产生。因为且不提对于与我们有关的那些人的殷勤,对于在这个小圈子以外的其他的人往往就是一种不正之风。假如一个人只采用这种推动力的话,那么这样一个人就可能会有一切的罪恶,——并非是由于直接的品性,而是由于他太喜欢讨好别人了。他会由于热心社交而成为一个撒谎者、一个帮闲者、一个酒鬼,如此等等。因为他没有按照普遍的良好行为的准则在行事,而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品性在行事,——这种品性其本身是美好的,但是当它不受控制而又没有原则的时候,就会是愚蠢的了。
因而真正的德行只能是植根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越是普遍,则它们也就越崇高和越高贵。这些原则不是思辨的规律而是一种感觉的意识,它就活在每个人的胸中而且它扩张到远远超出了同情和殷勤的特殊基础之外。我相信,如果我说它就是对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感觉,那么我就概括了它的全部。前者乃是普遍友好的基础;后者则是普遍敬意的基础。而当这种感觉在一个人的心中达到了最大的完满性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确实该爱他自己和尊重他自己,——但这是仅就他乃是他那博大而高贵的感觉所扩及于一切人之中的一个人而言。唯有当一个人使他自己的品性服从于如此之广博的品性的时候,我们善良的动机才能成比例地加以运用,并且会完成成其为德行美的那种高贵的形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