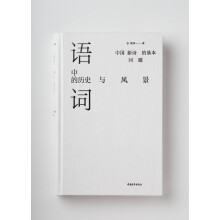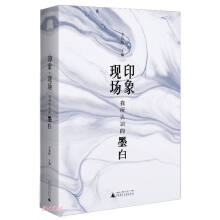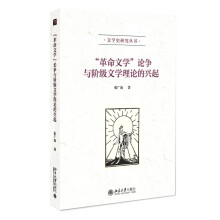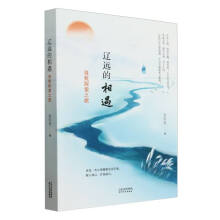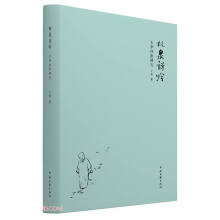《浪漫的灵知》:
第三是幻美,而幻美之为“美”,美就美在昙花一现,执手已违而去留无迹。古希腊是荷尔德林初始的爱和最后的爱,因为那是美的艺术之故乡。他笔下的许佩里翁说,从少年时代起,就更爱生活在爱奥尼亚、安提卡海岸,以及爱琴海美丽的群岛。“有一天真正步入青春之人性的神圣的墓穴,这属于我最心爱的梦想。”然而,这梦想之美,乃是幻美。荷尔德林的挚友黑格尔说,“古典文化是为人间至美”,乃是人类自然之外的第二天堂,即人类精神的天堂,人类精神“在此初露峥嵘,宛如初出闺阁的新娘,禀赋着自然天放的优美,自由自在,深沉而又安详”。然而,这是一种立足现代、参照古典而展开的对于失落世界的记忆与想象,如此幻美的世界也只能是一个永远不能回归的永恒天国。荷尔德林的希腊之旅,是对审美主义万神庙的朝圣,是为人类未来的黄金时代而设计的一个基本象征。它注定是虚幻的,幻美导致幻灭,幻灭又激发诗人驰情入幻,浪迹虚空。
于是有了第四——悲剧,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悲情,而是悲剧。悲剧性(thetragic),源自一种无法征服、不可超越、不能回避的铁的必然,这种必然在古希腊称之为“命运”。荷尔德林的希腊朝圣之旅,从体验幻美而触摸悲剧,而发生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希腊文化之伟大,恰恰在于它悲剧伟美与庄严,而不是柔和与秀美,故而荷尔德林的悲剧乃是绝对的悲剧。荷尔德林从1800年起开始翻译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注疏品达的颂歌,还三度抗争,书写哲学悲剧《恩培多克勒斯》。这一切努力都只留下了断章残句。未竟之作,就意味着情缘未了,此恨绵绵,这恰恰也是浪漫诗风的真谛。
18世纪19世纪之交,荷尔德林一口气写下了五大“哀歌”,在上帝转身忧叹的荒芜黑夜时分抒写绝对的心灵悲剧,为诸神复活预备审美灵韵流荡的空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