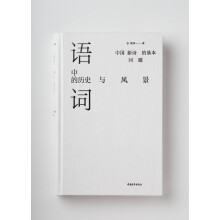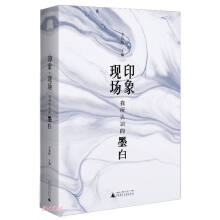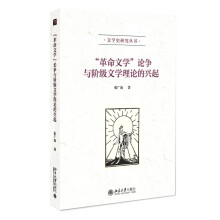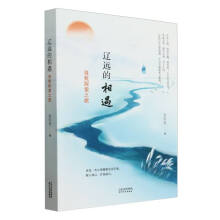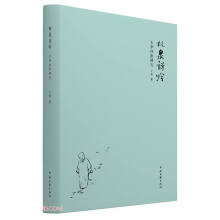文学的永恒性问题曾经是一个人们忌讳的敏感问题。尽管有些人不愿从理论上承认它,但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就迫使人们去思考它,解释它。回顾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的有关讨论情况,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印象,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从两个途径进行,第一种途径是在作品中寻找不朽的原因,由此提出几种解释:一是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因素发展缓慢,且有明显的继承性和普遍性,容易引起不同阶级、民族、时代的读者的共同美感;二是认为文学作品只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的真实,就具有永久的认识价值,文学的不朽魅力就存在于它的永恒的认识价值之中;三是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如果表现了普遍的人性和人情,这个作品就能不朽。第二种途径是在读者身上寻找不朽的根据,由此提出几种解释:一是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除了阶级关系外,还有非阶级的关系,人们毕竟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里,在利益、需要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此不同阶级的人也能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这是文学普遍性、永恒性的基础;二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社会的统治思想,不同阶级的人思想上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某一阶级成员对不同阶级的作品产生共鸣,实际上是接受另一阶级思想影响的表现;三是认为艺术是感情的领域,而感情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阶级的人虽然思想观念互相对立,但在感情上却可能相通。
以上种种解释,曾经展开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如从方法论上考察,争论各方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企图寻找一种不变的因素,以某种客观存在的不变性来解释文学作品不朽的生命力。这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点上的:艺术魅力的产生是按照刺激→反应的公式进行的,也就是说,作品的某些美学因素作用于读者,读者心里就引起相应的美感反应,就像一块石子投入湖中激起一阵涟漪一样。因此,艺术魅力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现象就只能在刺激物和反应主体两个方面寻求解释。从上述认识基点出发,必然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作品既然能打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读者的心,就说明这个作品包含着某种能打动不同阶级、时代的读者的属性。于是,剩下的只是对这种客观存在的不变性的不同解释了。但是,上述刺激→反应的公式是机械论的公式,企图用某种不变性来解释艺术生命力的方法显然是违反辩证法的。生命在于运动,一个作品的艺术魅力是一个复杂的生成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到艺术生命力的运动形式中去寻找它的不朽的秘密。
艺术的生命力是审美系统中主客体对立统一的运动形式,孤立地考察审美客体一方或审美主体一方,无法完满解释这种运动本身,而必须深入考察作品艺术生命的运动过程,揭示这种运动的内在机制。优秀作品具有普遍、永恒的魅力,这种魅力绝不是这些作品预先具有的能够消融阶级、民族、时代的隔阂的一种神秘力量,而是在文学欣赏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审美系统超稳定结构的功能特征。
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是方向相反的两种审美创造。文学创作把生活形象改造成作家的经验与心灵的表现形式,而文学欣赏则把作品的艺术形象改造成读者的经验与心灵的表现形式。作为作家的创造物,文学作品无疑是一种观念形态,是具有审美形式的特殊精神产品,是物态化的审美意识。但是,文艺欣赏是审美再创造的系统,每一个真正的欣赏者都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的观念内容,而是借助于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情感的形式进行审美再创造,来表现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在这里,欣赏者实际上是把作品当作表现自己的经验和情感的普遍形式(一种广义的符号)来利用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这几乎是文学欣赏的普遍现象。凡是能引起共鸣的作品实际上都起着唤醒读者的经验和激发读者的情感表现的作用。在这里,文学作品获得了符号的性质。因此,在文学欣赏中,文学作品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它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超意识形态的抽象形式,即符号。
为了进一步弄清文学作品的这种二重性,我们必须考察文学作品的传达系统。毫无疑问,文学作品是对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的传达,文学活动就是通过这种传达而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学作品的传达系统包含着三个子系统:一是概念逻辑体系,二是艺术形象体系,三是表现形式体系。它们分别给读者的神经系统传输三种类型的信息,即语言信息、形象信息和形式信息。这样,文学作品的传达过程就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概念逻辑的传达,它传达作家的理性思考,作用于读者的理知世界,以其确定性的概念和推理形式充实读者的智力。这种传达是以告知的方式来实现的。二是艺术形象的传达,它传达作家的经验和情感生活内容,作用于读者的情感领域,唤醒那些尚未成形的、难以言喻的经验和情感,使其成体和获得表现。这种传达是以象征的方式来实现的。三是表现形式的传达,它传达作家的生命运动形式,作用于读者的生理—心理结构,起着调节读者的生命运动形式的作用。这种传达是以暗示的方式来实现的。
总之,文学作品就是通过告知、象征和暗示这样三种方式共同完成传达任务的。在这个传达系统里,三个层次的信息传递过程是各不相同的。在第一个层次,作家的理性思考的内容是以显露的、确定的概念逻辑的形式出现的,它可以直接作为读者知性的加工材料,无须借助其他中介。在第三个层次,作家的生命运动形式与读者的生命运动形式是直接对应的,作品的表现形式就是读者直觉的对象,因此也不需要借助其他中介。这就是说,上述两个层次的传达过程,信息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前者是以语义信息提供自由选择,后者是以两种运动形式的直接契合来吸收信息。但是,第二个层次的传达过程,情况就不同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不是直接的,它们中间横着一个中介——形象体系。于是读者就必须通过对形象体系的意义的把握才能与作家会意交心。这个形象体系是作家观念内容的外壳,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域是宽泛而模糊的。读者要接近作品内在的观念内容,就必须超越形象体系的不确定性。因此,读者就要调动自己的经验存贮和想象功能来理解和补充它。而当读者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把作品的形象体系作为表现自己的经验和情感的媒介。从这里不难看出艺术交流活动的实质:一方面是作家用形象符号系统作为外壳巧妙地包裹着自己所要传达的观念内容,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读者为了超越形象符号系统的不确定性,却把它作为生发自己的经验和情感的外壳,即表现的媒介。这就是说,在文学欣赏中,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成了读者进行审美再创造的契机和触媒。正因为这样,一个作品的审美意象所提供的语义信息量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审美再创造的空间到底多大。一个作品的符号性越明显,越能激发读者的审美再创造,那么读者就越能超越观念的疏远性,实现与作家的经验和情感的交流。总之,正是因为文学传达系统的上述特殊性,文学作品才具有观念性与符号性统一的两重性特征。弄清文学作品的这种两重性,是理解优秀文学作品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关键。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文学作品的两重性是沿着相反的方向互相转化的。具体地说就是:作家运用一定的艺术符号反映生活和表现思想感情,从而创造出具有审美意义的作品(观念形态)。符号性就消融在观念性之中(一个优秀的作品必须让读者看不到人为痕迹)。这就是符号性向观念性的转化,手段向目的的转化。这样,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就是一种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而读者在文学欣赏中则又把艺术形象转换成表现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内容的符号。这就是观念性向符号性的转化,目的向手段的转化。文学作品一进入审美系统之后,它就经历这种转化,而且只有首先转化为符号,才能被众多的读者所利用,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优秀文学作品具有普遍、永恒的魅力,其秘密就存在于观念性向符号性转化的运动之中。
在文学欣赏这个系统中,作品、读者、环境,是三个主要的结构元素。文学欣赏的过程就是这三者的协调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文学作品才获得生命力。但是,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是因人而异的,其中最基本的则是阶级的、民族的和时代的差异。因此,作家与读者之间在经验和思想感情上会产生巨大的分化。文学作品作为作家的观念形态,与读者的观念世界本质上具有疏远性,前者很难直接成为后者情感的对象。欣赏者总是以能否满足自己情感的需要为准绳来选择欣赏对象的,对人的情感需要毫无关系的事物,人们对它就毫无美感可言。只有那种能成为人的情感对象的事物,才可能引起人的美感。可以说,“感情只是向感情说话”(费尔巴哈语)。而文学作品要成为读者情感的对象,就必须在欣赏系统中实现元素的互相过渡,使作品与读者获得同一性。这种过渡的可能性就在于文学作品的二重性特征,即观念性与符号性的统一。观念性是作品这一系统元素的个体性,符号性则是它的普遍性。作品进入文学欣赏系统后,必须扬弃它的观念性,成为读者审美再创造的媒介,作品才能向读者过渡,成为读者情感的对象。这就是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必须首先过渡成为激发读者展开经验联想和情感表现的符号,读者借助这种符号的媒介重新创造一个渗透着读者自己的观念内容的审美意象。这个新创造的审美意象才是读者情感的真正对象。外国谚语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充分表现了这种过渡。在这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哈姆雷特形象,已经过渡为这“一千个读者”进行审美再创造的共同媒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符号)。每个读者都在借助哈姆雷特形象的普遍性形式重新创造自己心目中的哈姆雷特意象。这意象才是各个读者情感的对象。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创造的哈姆雷特形象所蕴含的观念内容并不是直接成为读者的对象,这个形象在文学欣赏中经历了上述过渡之后才与读者构成同一性,而成为文学欣赏系统中的一个有机元素。这种过程是十分隐蔽的,无法用直观的方法来揭示,而必须借助辩证思维。
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文学作品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但又可能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而产生普遍、永恒的魅力。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矛盾现象乃是导源于文学作品的二重性。文学作品作为观念形态,无疑要打上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烙印,但在文学欣赏中,它经过扬弃过程,由观念性向符号性转化,成为读者进行审美再创造的共同媒介。因为符号具有工具的性质,正如语言可以为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人所利用一样,优秀文学作品的符号性能够使它成为不同阶级、民族和时代的读者表现自己经验和情感的共同形式,因而能超越它自身观念内容的局限性,具有普遍、永恒的生命力。总之,文学欣赏的基本运动形式是:文学作品在空间横向和时间纵向上不断被读者群体改造成各自的经验和情感的表现形式(符号)。因此,优秀作品的普遍、永恒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是文学作品的符号性的普遍、永恒的功能。
如上所述,在文学欣赏中,文学作品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由观念性向符号性的过渡。这种过渡使作品能够超越自身观念内容的个体性的局限,成为激发读者群体进行经验联想和情感表现的普遍形式。因此,作品与读者就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即作品成为读者经验和情感的象征。所谓“象征”,它的基本含义是用某种知觉或想象的图像标示或暗示某种不可见的意蕴。但这里指的不是一种艺术手法,而是作品与读者的一种联系方式。这种“象征”联系方式具有如下一些特点:首先,象征联系的建立是以结构特征的相符度为基础的,而不求质的完全契合。比如松树象征豪情,竹象征正直的人格。在这里,松树与豪情、竹与正直人格都具有不同的质,但在力的结构上却是相对应的(松树的壮阔、伟岸的形象与豪情的特征相似,竹的笔直凌霄的形态与正直的人格在结构特征上相对应)。其次,象征者是具体的图像,而被象征者则是难以言喻的意蕴。第三,象征活动往往是不自觉进行的,是在凝神观照的条件下,经由想象和联想的中介直接产生的,而不是通过推理性过程实现的。总之,象征与比喻、寓意等都是一种异质同构的联系,但它们有不同的特点。比喻与象征的区别比较明显:比喻是意义性的,即用人们熟悉的具体事物使被比事物的意义显露出来,而象征则是精神性的,是为了激起某种精神反应。寓意与象征也不同,寓意是“过渡性的”、明显的,它标示某种与它不相干的东西;而象征不是过渡性的,也是不明显的,它没有失掉自身有意义的本质。寓意表示得直接,它唯一的职能是传达某种意思;象征首先是自身,其次才是暗示出某种意蕴。在文学欣赏过程中,作品与读者建立起来的基本联系也是异质同构的。这是因为,作品的内容是作家在特定情境下的审美感受,它是个体性的。由于阶级、民族、时代以及个人经历和气质的差异,读者的观念世界与作品的观念内容必然是异质的,读者的心灵并不是像一面镜子一样毫无保留地反映作品的观念内容,同一作品很难与不同的读者建立同质的联系。但是,由于作品在欣赏过程中发生了观念性向符号性的过渡,符号是一种普遍形式,因此它就与读者群体的审美心理普遍建立一种结构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异质同构联系了。它是文学欣赏过程中建立的普遍联系,因此我们就借用“象征”的概念,以此来揭示文学欣赏中主客体辩证运动的原理。
现在让我们看看文学欣赏的实际情况。在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欣赏中经常可以遇到如下几种现象:一是艺术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行和借代。例如冈察洛夫塑造的奥勃洛摩夫形象成了一切怠惰、害怕变动和无力从事任何有益的实际工作一类人的代名词。列宁曾说过:“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在这里,奥勃洛摩夫的形象实际上已被抽象为一种性格模式,然后由联想作用而引起一系列的类比。二是意蕴延伸。例如《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中曾谈到,马克思同意海涅如下的观点:“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马克思补充说:绝不应该把这种新的解释看作“歪曲”,看作对一种理论创建时或一部作品产生时建立的不变准则的背离。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一文里,谈到续承托翁的文学遗产,目的在于使人民“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政府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在于“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新社会”。这些思想并不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原有的,而是从托翁作品中对俄国社会的深刻反映所蕴含的意蕴中延伸出来的。这种延伸表面看来是一种推理活动,实际上是建立在托翁作品中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出来的经验联想这一基础上的。三是情感共鸣现象。这是文艺欣赏中最常见,几乎人人都有过的体验。但是共鸣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呢?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共鸣是情感的契合引起的,但我认为它只是情感的异质同构联系的表现,是建立在象征联系基础上的读者对作品的肯定性情感反应。以上三种现象就是文学欣赏中审美主客体的异质同构联系的三种表现。这种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异质同构的象征联系就是文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根本原理。
文学欣赏过程中象征联系的建立是以读者的象征欲求和作品的象征功能为基础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