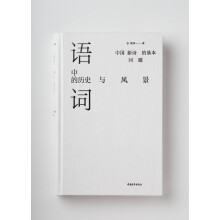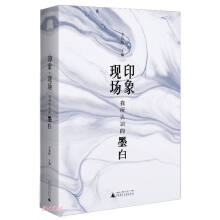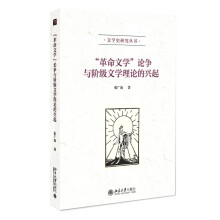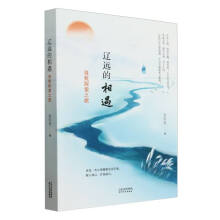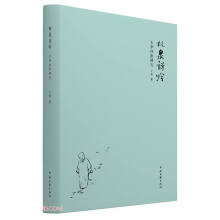1.有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需要深入辨析。我们常说,华文文学是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相同的一种语系文学。这是就语言的世界性存在现象而言。然而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种语言的世界性存在有两种情况,在诸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这些在“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的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粹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显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异国文化的遗锐。”华文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播与存在,不是“殖民宗主国”的“文化遗蜕”,其性质与此完全不同。
华文是伴随着19世纪以来华人的海外迁徙,而大量播散世界的。其时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殖民主义的侵扰,迫于生计而无奈谋生异邦的华人,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到同样处于殖民压迫下的欠发达国家,都是弱势族群,华文在华人所居国的语言和环境中,也都是弱势语言和弱势文化。即使由于华人的刻苦奋斗,在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甚至在某些国家,华人经济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强势经济,但仍无法改变华人在所居国中语言和文化的弱势地位。这一状况无论在华人政治、经济都处于弱势的欧美诸国,或者在经济略居强势的某些东南亚国家,都是一样的。华文首先是作为移居海外的华人族群保留母语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存在的;其次才通过华人的文学书写,成为他们铭刻自己几近衰亡的族群记忆,再现从国内到海外的双重生存经验而获得精粹体现的。华人的华文书写,是一种母语书写,而其他受到西方殖民的国家对宗主国语言的书写,则是一种被迫的非母语的书写。即使在殖民势力溃退之后,依然无法摆脱这一后殖民的文化遗蜕。前者是伴随移民的语言移入,是移民主体对于母语的语言行为,在所居国的语言环境中,是一种弱势语言;后者则是伴随殖民而来的语言“殖民”,是殖民者强加于被殖民者的语言霸权。二者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2.20世纪中国的海外移民,就其身份认同而言,大致经历了华侨——华人——华裔三个互相交错的发展阶段,它们相应地界定了不同历史时期海外华文文学的性质、特征和文化主题的变迁。早期的中国海外移民,大多没有放弃原乡的国籍,或实行双重国籍。他们因之被称为华侨,因此,华侨的文学创作,可以视作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但当中国的海外移民,在取消双重国籍认同,而选择了所在国家的国籍之后,他们国家认同的政治身份已由华侨变为所在国公民的华人(或称华族),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虽然在文化认同上不一定出现根本的变化,但已经不能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了,而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学构成的一部分。早期的华侨和后来的华人,在其移居的国家或地区,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族群。他们以文学叙述的方式参与弱势族群族性记忆的建构,使二者在文学的文化主题上,有基本一致的一面,例如强调对于原乡文化的承袭,普遍抒写着怀乡思亲的文化情绪,等等。这些题材和主题的普遍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能把所有海外华文文学抗拒族性失忆的自我历史建构,都当作文化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二者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从华侨到华人,还面临着另一个在国家认同之后更深入的文化适应和新变问题,即华人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涵化,这是海外华人文化生存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同时也呈现为进入“华人”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化主题上与华侨文学不同的变化与发展。而对于华裔,即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几乎已经完全适应或被“本土化”了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无论用华文,或用当地语言写作的文学,较多地表现为站在所在国主体文化的立场上,重新消解、利用自己固有的族性文化,在移植、误读和重构中,作为少数族群自身的一种文化资源,参与到所在国多元的文学建构之中,表现出不尽相同于“华人”时期新的文化精神与文学特征。
3.五四的新诗革命(新文学亦然),并不仅只是语言和文体的革命。从上一个世纪开始,国势的颓危和国力的贫弱,使中国这个东方的古老帝国,在西方凭借工业革命崛起的列强面前,变成被宰和待宰的羔羊。民族衰亡的危机,唤起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救亡行动。而欲救亡,必先启发民智;要用新思想新精神启蒙民众,则须先打破已经僵死了的语言形式,寻找新的运载工具。在五四新诗的肇始者那里,这个思路是十分明确的。因此,胡适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讨论他的新文学构想时提出的八项主张,就包括了“不用典”等五项“形式上之革命”和“须言之有物”等三项“精神上之革命”。待到1917年1月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便把“精神上之革命”的三项主张移在了“形式上之革命”的五项主张前面。在1919年发表《谈新诗》中他说:“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920年,在《尝试集·自序》中又说:“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到了为《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时,他更简练地表达了自己文学革命的理想:“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而“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他方面。”(《逼上梁山》)可见,当时文学革命的发动者是十分明确,自己所进行的语言、形式的革命,是为了实现启蒙、从而达到救亡目的的精神上的革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