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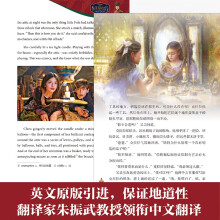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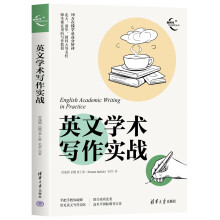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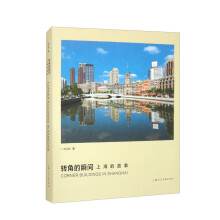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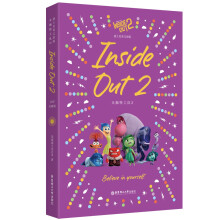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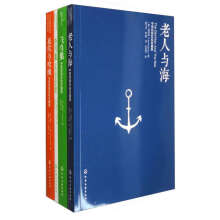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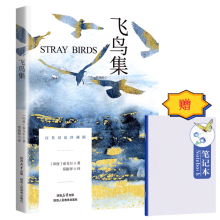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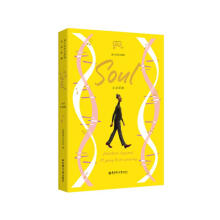



《茶花女》讲述了一个青年人与巴黎上流社会一位交际花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一个妓女的爱情悲剧,揭露了法国七月王朝上流社会的糜烂生活。对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提出了血泪控诉。
我从几个知晓她弥留之际境况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玛格丽特在她长达两个月的无比痛苦的病危期间,谁都没有在她的床边给过她一丝慰藉。
此后,我的视野从玛侬和玛格丽特的身上,转到其他我所熟知的那些女人身上,我看到她们一边歌唱,一边走向永恒不变的死亡。可怜的女人啊!如果爱上她们是一种过错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对她们报以同情。你们会同情见不到阳光的盲者,会同情听不到大自然声响的聋子,会同情无法用声音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哑巴,但是在一种假惺惺的毫无廉耻的借口之下,你们却不愿意同情这些心灵上的失足者,以及灵魂上的聋子和良心上的哑巴。这些残疾使病痛中不幸的女人变得发疯发狂,使她无限忧伤且又无法体味出善良,听不到天主的召唤,也讲不出爱情和信仰的纯洁语言。
雨果塑造了玛丽翁.德.洛尔姆,缪塞创造了贝尔娜雷特,大仲马塑造了费尔南特,历代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把仁慈的怜悯之心奉献给青楼女子。有时候一个伟人挺身而出,用他的爱情甚至他的名声来为她们恢复名誉。我之所以要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以后那些会来品味我这本小说的读者之中,恐怕有很多人会把它丢在一旁;他们担心这会是一本专门为邪恶和淫欲辩护的书,而且该书作者的年纪想必更容易使人产生这种疑虑。希望这样想的人会改变他们的初衷,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顾虑,那还是请继续看下去吧。
说实在的,我只信奉如下原则:对于没有接受过善良熏陶的女人,天主几乎总是给她们指引着两条道路,引导她们走向善良:一条是痛苦,一条是爱情。这两条路走起来都步履维艰。踏上这两条征程的女人,往往在上面走得两脚鲜血淋漓,双手皲裂。此外,她们也把罪孽的华丽饰物留在了沿途的荆棘上,赤条条地抵达目的地,而这样一丝不挂地来到天主跟前,是用不着羞涩的。但凡与这些勇敢女子邂逅的人都应该帮助她们,并且不妨直截了当地对大家说,他们曾经遇见过这些女人,因为在将这些事公之于众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指明了出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草草了事地在人生道路的入口处竖上两块牌子:一块是告示牌,上书“善之路”;另一块是警告牌,写着“恶之路”。也不能对那些来到入口的人说:“挑一个吧!”而必须像基督那样,指引出路,把那些容易误入歧途的人从后一条路带往前一条路;尤其不能让这些道路的开端显得过于险峻,崎岖难行。
基督教关于浪子回头的动人劝谕,目的在于教导我们对人要仁慈,要宽大为怀。耶稣对那些饱受情欲之害的灵魂充满了爱,他致力于包扎他们伤口的同时,从伤口本身挤出治疗伤口的香膏敷于伤口之上。故而,他对玛特莱娜说:“你将得到宽恕,因为你爱得太多了。”这种崇高的宽恕,应当唤醒一种更崇高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比基督更严厉些呢?这个世界为了要显示它的强势,故作严厉,我们也就固执地接受了它的偏见。为什么我们要和它一样抛弃那些伤口流着鲜血的灵魂呢?这些伤口像病人渗出污血一样,把他们过去的罪恶都渗出来。这些灵魂在等待着一只友好的手来包扎他们的伤口,治愈他们心灵的创伤。
我在向我同时代的人呼告,向那些认为伏尔泰先生的理论已经过时的人进言,向像我一样懂得十五年来人道主义正突飞猛进的人进言。分辨善恶的真谛已经得到公认,信仰又将重新确立,我们对神圣的事物又开始顶礼膜拜。如果这个世界算不上十全十美,至少可以说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凡是聪明人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一切伟大的意志都服从于同一个原则:我们要心地善良,要朝气蓬勃,要真心实意!邪恶只不过是一种虚无的幻境,我们要为行善而感到骄傲,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丧失信心。不要轻视那些既不是母亲、姐妹,又不是女儿、妻子的女人。不要锐减对亲眷的尊重和对自私的宽宥。既然上天钟情于一个忏悔的罪人,而不是更喜欢成百个从未违反戒律的人,就让我们竭力讨上天的欢喜吧,上天会赐福给我们的。在我们行进的道路上,给那些被人间欲望所断送的人留存我们的宽恕吧,也许对神圣的期盼可以拯救他们,就像那些善良的老妇人在劝说别人接受她们的治疗时所说的那样:即便没有什么疗效,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当然,我想从我微不足道的论题中引出深刻的结论,似乎显得过于胆大了,然而,我却是这样一种人,相信一切浸于微末之中。小孩子虽然幼小,但他却是未来的成人;脑袋虽小,但它却蕴藏着无限的思想;眼眸只不过是一个圆点,但它却能环视辽阔的天地。
温馨提示:请使用中新友好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