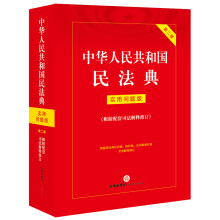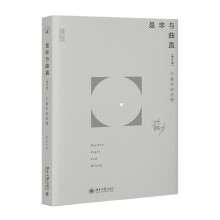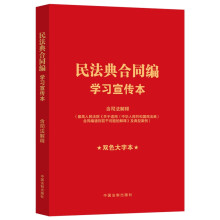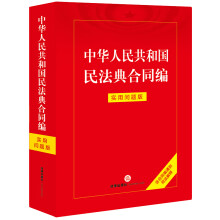概念的界定,不是具体的文字工作,而是立法中最具有政策性的系统工程,不突破立法文本的文字表达的局限,就无法准确界定法律概念。
一、精准切入
法律概念的界定,切人的角度很重要,即从哪个角度着手描述。
2009年《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字面上看是在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实质是从条件这个角度进一步描述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核心概念。但就法律规范而言,除少数理论研究者,绝大多数守法者、执法者、司法者或者是像笔者这样的实务研究者,并不关心这些条件本身,只关心这些表述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事主体及其行为。
《民法典》第143条给出一个现成的,目前看来最优的选项:“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即直接规定哪些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这是在明确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后,需要进一步落实的最重要的内容。立法从这个角度切人,不再绕行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就选准了切入点。
站在新的切入点看原条文的表述“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方面,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的合意行为,为何非要具备下列条件?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即使不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行为,不是照样会产生法律效果?事实上,绝大多数不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行为也都会执行到位,即发生其法律效力;即使没有落实到位的,只要民不举,也不会有人知道。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必要强调民事法律行为非要如何,只需要规定如果不遵守民事法律行为要求会有何种后果即可。
另一方面,虽然法律明确要求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但不符合要求怎么处理?这又需要进一步规定。也就是说,立法应当明确的是规则,即出了问题如何处理,而不只是提要求。
二、认识到位
概念界定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确、准确,实现这一要求最基本的前提,不是表述的华丽,而是认识的深邃:认识提高了,表述自然容易;没有洞明概念的本质,怎么表述都让人觉得不得要领、不得其法而无法入门。
概念定义时实现精准切入的关键,不在意愿,而在对目标概念的认识深度。2009年《民法通则》第66条第4款的表述相当冗长:“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这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四重关系:行为人是无权代理人,与其共同实施民事行为的人、他们的身后还有被代理人以及受害的他人。此时,第三人究竟指代谁,要看从哪个角度着眼,或者说从哪个方向开始数,因此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很容易数错。不如将与行为人共同实施行为的人,即直接与行为人相对的人,称为相对人。《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规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用相对人替代第三人,初步理顺了这几层关系。更重要的是,《民法典》第171条的表述只提到了相对人与行为人二者。
事实证明,无论在理论上、学理上、法理上,还是今后守法、司法、执法的现实中,无权代理概念的概括力都太强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替代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从而大大避免了表述冗长和语义错乱。
三、词义通达
《民法典》第58条第2款将2009年《民法通则》第37条第3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中的场所改为住所,纠正了《民法通则》中一处明显的不妥之处。在《民法通则》此前条款早已围绕住所规定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再出现场所必然会有人问场所与住所是什么关系?显然,场所是个普通名词,就是指某个地方;住所则是个法律概念,在已经对住所有明确界定和广泛适用的情况下,必须用其全面替代场所。
2009年《民法通则》第15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其中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重复了两个“地”,仍没有解决“所”的问题:字面上看,仍存在着以地为所的逻辑和表达错位。这种形式上的错位,是内容表述不清的直接反映。
《民法典》第25条强调居所与住所的对应:“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解决了我国立法几十年来对住所本质的误解:住所是个位置概念,不是地域概念,其法律意义是为了方便查找,以便完成送达等法律程序,因此越具体越好,最好具体到“门”。而我国此前的立法强调户籍地,虽然通常情况下户籍所在地也是以户籍登记为准的,但毕竟没有把这个问题厘清、说透。
居住地仍是一个地域概念,一般人会理解为一个大地方而不是一所具体的房子。《民法典》明确并反复使用居所,解决了“住”的行为与法定处“所”的衔接问题,进而指向住所就顺理成章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