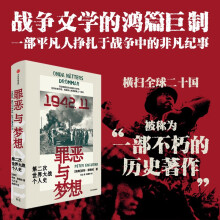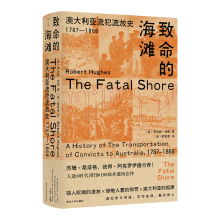尽管这些精英被称为奴隶而不是护卫者(guardians),但这并不重要。国家拥有他们,同时,他们也掌控国家。精英统治的职业模式强化了他们服务国家的信念;同时,他们被从具有不同地理环境、民族,甚至是宗教和肤色的地区招募而来,由此造成的相互之间的差异提高了他们的忠诚度,或者,至少减少了他们试图谋反的邪念。像那些“野心膨胀”的酋长最初依靠的权力基础——部落民一样,这些精英出自艰苦的生活环境,并且,被隔绝在那些令城市统治者堕落的温柔陷阱之外。不过,与聚集在一起生活的部落民不同,他们被割断了与亲属之间的联系。
如果这样的体制没能持续运转下去,那么,它衰败的原因可能正如柏拉图所预见的那样:尽管,这一统治集团最初的凝聚力通过有意地严苛训练锻造而成(而不像部落民那样,其凝聚力因共担沙漠中的风险而产生),但最终,他们还是拜倒在了荣誉、亲属关系以及财富的引诱之下。这是一种柏拉图所预测的,如同在其他政治体的交替衰败中所展现的那样,诱惑操纵其命运的规律。当然,真实的衰败过程不会像论述的那样规整。印度的种姓制度(Hinduism)可能是践行柏拉图主义(Platonism)的另一种类型,其形成了一个具有学识、实行高压统治,并能自我延续的固定阶层,不过,其完全服从于血缘关系原则。因此,马穆鲁克体系是唯一的柏拉图主义变体。柏拉图主义的关键要素:教育、隔离、与财产隔绝、断绝亲属关系,全部存在于该体系之中。
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在官员产生方式上,马穆鲁克体系是一种特别的、超越其时代的尝试。由于传统社会中总是存在一种试图攀附地域与亲属关系的积习,这使人们逃避责任、漠视法令,并且导致国家分裂成自治的地区单元,因此,传统国家在其中央集权化道路上倍受阻碍。而只有可能在现代社会,由于众多因素——社会总体的原子化(atomization)、广泛的工作与职业方向、人们在学校而不是在地方团体中得到社会化——的共同作用,才在本质上把每一个人转化成潜在的官僚。就总体而论,在当前可以相信,人们通过官僚组织的方式执行各自的任务,而不会为了讨好他们的亲属而使规则发生扭曲。可以说,现在我们都是马穆鲁克。然而,传统社会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为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奴隶、阉人、教士或外国人,以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当马穆鲁克原则及其修正形式取得大规模的显著成功时,或许应当反思的是,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所谈论的政治体是否可以归类为部落国家?例如,以部落国家这一术语来称呼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就确实是一件荒谬的事。那是它的开端,但是它并没有保持那种形式。马穆鲁克原则是一种可以代替部落基础的方案,两者的纯粹版本构成了一个范围的两端,在中东,恰好位于两端的社会形态十分罕见,许多政治体处于这一范围中间的某个位置。
这样,便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奥斯曼国家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伊本·赫勒敦有关中东社会的理论(我已深深依赖这种理论)已经失效?它是否已经无法作为一种适用于穆斯林世界干旱区域的总体理论而存在?对此,我并不这样认为,理由如下:毫无疑问,在中东,两种因素(伊本·赫勒敦所论述的部落基础范式与其对手奴隶官僚范式)能够并且确实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各种国家形态之中。
在其初始阶段,奥斯曼帝国不过是安纳托利亚的一群典型部落政治体,仅仅当它们中的某一群体取得突出成就时,下述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才得以发生:其一,它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西部,最终在尼罗河谷获取了一个由温顺的定居农民组成的特殊基础;其二,马穆鲁克因素疯狂生长,不断消除与其竞争的部落因素。这两种变化无疑紧密相关。大批可供征税的农民维持了非部落国家机构的运转,而农民不适合由部落民来治理。然后,这种体系以一种自发的形式在突尼斯、阿尔及尔以及其他可能的地区进行自我复制。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