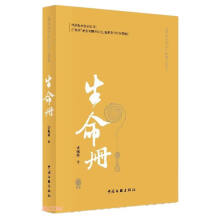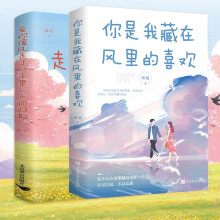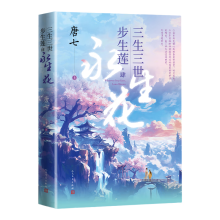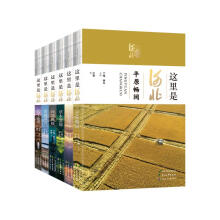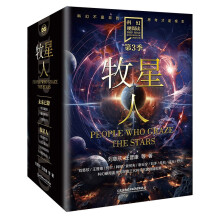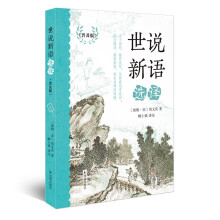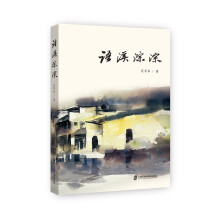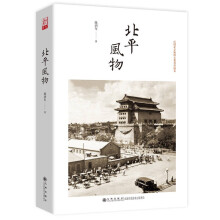《大明权斗之大内锦衣卫》:
那少年听见人们在大呼小叫,便往那堆人处走去,那中年人紧紧跟上。他们刚走到人堆前,斜刺里忽地闪出几条壮汉。他们的衣着不一,都是民间常服,但都穿着一件黄色的对襟罩甲,这种衣服军民士卒皆不准服用,惟骑马者可服,而黄色罩甲连骑马者也不可服,惟军中骑马者可服,其衣式较短,为正德年间刚刚启用。几条壮汉并不说话,只是彼此间递个眼色,便横着肩膀上前,稍一发力,就在人堆中连挤带别地闯出了一个口子。
那少年上前,踮起脚尖,顺着口子向里看了一眼,见是一座龙山,闪出无动于衷的表情,掉头便走。他走着,一副对四周事物漠不关心的样子,唱戏的、踩高跷的、各种日杂商品从他眼前掠过,他除了扭头回顾外,毫无表情,只是有漂亮的少女从他眼前经过时,才能惹得他回头看上几眼,即使这时,他的嘴也要紧紧地抿着。这种无动于衷,从他的脸上移到了他的身上,渗到了他那优雅懒散的动作上,甚至会在衣服的每条皱褶上表现出来。
一通锣鼓,压过了其他嘈杂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眉心微微一动,见不远处,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一堆人,便又懒懒散散地走了过去。没走到人堆前,几个穿对襟黄罩甲的壮汉,便急促地从他身边绕过,几个人在人堆边缘挽起袖子,露出膀子,打头的悠着劲,一拧身子,挤出了一个空,几个人往里一游,便不惊动旁人地开出个一尺来宽的小过道,那少年和那妇人般的中年男人随即侧着身子挤了进去。几条壮汉原以为那少年照例是看上两眼便走,谁知道他这回只是一味地呆着,不挪窝了。
场子中有两个汉子,长相挺相似,像是亲哥俩儿。挺冷的天,俩儿都穿着白色的棉搭护,这是元代遗留下来的一种衣式,半截袖,比褂子略长,腰当间束一根半尺宽的大红帛带,练把式的人喜服。
俩儿一个拿锣,一个拿鼓,连敲带吆喝。
年长些的那位,圆头圆眼肉鼻子,脸色乌油油的,有痘瘢;下巴宽大,嘴唇没一点曲线;脖子短,几乎和头一样粗,个子不算高,背脊阔得异乎寻常。肩头和手臂一抖一抖的,现着不祥之兆。
他“当”地敲了声锣,随即厚墩墩的大巴掌往锣面上一摁,爆出了一嗓子:“俺两个是哥俩儿!”
另一位击了声鼓,亮开了嗓门:“俺哥叫刘宠,在家排行老六,又叫刘六!俺叫刘宸,在家排行老七,又叫刘七。”
他除了个子比刘六略高些外,别的没啥不同,只是表情显得聪颖些。
刘六吆喝道:“俺哥俩儿打霸州来。霸州在哪儿?距京师不远,快马只需一天的工夫。”
刘七接道:“来京师做什么?来京师拉场子。拉场子做什么?分文不挣!这位要问啦,分文不挣还拉场子,那图个什么呢?”
“只图个以武会友!”刘六又接了过来。说罢,“当当当”敲了阵锣,末了站定亮相,那架势像个粗墩墩的老树桩子一般。
围着的人好奇地看到既拉场又宣称分文不取的哥俩儿。
静默中,冷不丁冒出句尖声细气的问话:
“霸州来的哥俩儿,你们的话让我好生纳罕。容我再冒问一句,你们这时候来拉场子做什么?”
问话的正是那个微胖、如同女人一般的中年人。他把那少年挡到身后,抢上一步,等着回答。
刘六瞥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刚才说了,俺哥儿俩只图个以武会友。”
“那以武会友又图个什么?”中年人似笑非笑地又来了一句。这时,他那对耗子眼泛着贼光。
“以武会友是图……”刘六被噎住了。
中年人等着回答,眼睛像月牙般弯曲着。他右手轻抚着左边的面颊,那儿有一个充满着血筋的肉瘤。
“这位看官,以武会友就是以武会友嘛。”刘七看刘六答不上来了,乐呵呵地接过了话,“这会儿说这话,还不是为了叫列位看官放心,大过节的能不花钱瞧个乐子。”
刘六被提醒了,一扬脖子,“就是这么回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