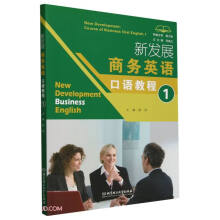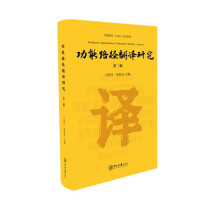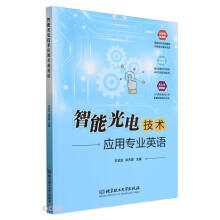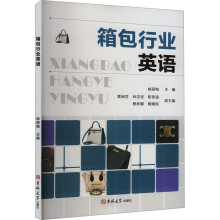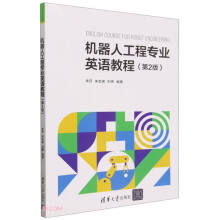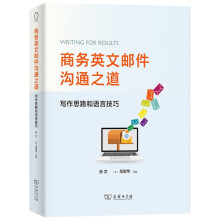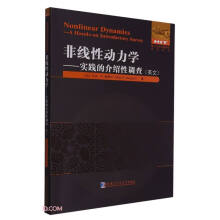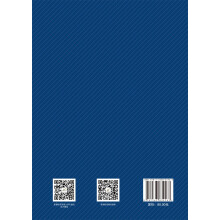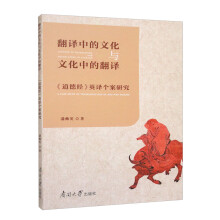第1章 导论
1.1 引言
商务英语通用语(English as a business lingua franca,BELF)交际中的元语用话语(metapragmatic utterances)体现语言使用的反射性(reflexivity),具体表现为来自不同母语文化的交际者,对交际进程与效果进行协调适应的意图与努力,如例1-1中的黑体部分(例子选自维也纳—牛津国际英语库,VOICE 。“S1”代表Speaker1,其余依此类推。)。
例1-1(选自会议PBmtg3)
S1: er (1) also i(’d) like to make c- comment that er (1) [first name1] was (.) he visited korea (.) e::r (.)
S2: march
S5: <6> march </6>
S1: <6> march </6> sometime in MARCH (1) er and we had a very e:r good discussion (1) e:r and e:r we agreed to (.) do some ACTIVE er activities (1) in convenience store (1) e:r but that means (.) the [thing1] (.) er in korea (.) in convenience store (.) was NOT successful as we planned
例1-1选自韩国经销商和德国生产商的一次关于产品销售会议中的对话,其中使用的元语用话语“i (’d) like to make c-comment that”预告后续话语内容,使与会者有所准备;“we had a very e:r good discussion”是对双方三月份会谈的积极评价,把之前讨论的内容激活,重新纳入当下讨论中,利于激活双方的共知基础,推进交际的进行;“that means”表达对观点重述的意图,引导对所述观点的理解。BELF交际中这类元语用话语的使用可以激活、寻求或创建相关语境因素,如交际期待、共同经历、良好意愿等,建构共知基础(common ground),对交际进程和效果进行协调适应,旨在完成交际任务。
元语用现象及其研究发端于1984年《语用学期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刊载的元语用研究专刊(何自然等,2006:289)。此后,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阐述元语用研究关涉的不同方面与层面(Caffi,1994;Mey,1993;Hübler,2011)、元语用意识凸显度(salience)与层级性(Verschueren,1995/2010,1999,2000;侯国金,2005,2011),以及元语用意识及其标识语(Grundy,2000;Verschueren,2000;冉永平,2005)等方面展开。也有研究对特定语言结构进行元语用分析(Bublitz & Hübler,2007;Ran,2013;蔡少莲,2006;吴炳章和张德玉,2012)。从研究视角看,多数采用语用学和功能视角讨论元语用意识及其标示语(如Verschueren,2000;Silverstein,1993),还有的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如Blum-Kulka通过对以色列文化中的礼貌现象进行元语用分析,试图发现礼貌的普遍性问题;Penz(2007)探究了在跨文化合作项目中元语用评论语对建构共知基础的作用;Dafouz-Milne(2008)基于媒体语料,研究在不同文化中,元话语标识语说服作用的异同。总之,元语用研究涉及宏观和微观层面,研究成果丰硕。但以往研究对BELF交际中的元语用问题关注不够,结合社会与认知两个纬度对其中使用的元语用话语的探讨更为少见。
BELF交际中的元语用话语受到独特的社会和认知因素制约,体现为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选择语言手段对交际进程与效果进行相互协调适应的意识与努力。英语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语言交际建构了语言使用的新语境,赋予语用能力以新的内涵(冉永平和杨青,2015),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一些关键问题逐渐取得共识。首先,ELF指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使用英语的交流活动(Jenkins,2011,2015;Seidlhofer,2011),BELF指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在商务场合使用英语进行交流。其次,ELF(包括BELF)不存在实体,而是一种语言实践活动、功能或交流方式(Alptekin,2010;Mackenzie,2014;Kecskes,2015;冉永平,2013),扎根于不同文化的互动之中,具有流动性、灵活性、相依性和混合性。另外,BELF研究已不再关注单一的“霸权”的英语,而关注不同的英语变体和相对频繁出现的语法和句法特征(House,2009;Mackenzie,2014),英语逐渐成为他者语言(冉永平和杨青,2015),多元标准和多中心论正在为人们所接受(武继红,2017),也即BELF正经历一个非本族化(non-nativisation)过程。总之,BELF研究不再致力于识别各种变体的共核特征(core features),而是探究交际过程的功能性和多元互动性(Kecskes,2015),即关注不同母语背景的交际者之间如何相互协调适应,容忍多元化的文化差异及多元语用语言现象,实现成功交际(冉永平和杨青,2015)。已有研究表明,在商务发言讨论中,BELF交际者要花比自己母语多26.5%的时间表达同样的思想(参见Hincks,2010),尽管如此,在共同的目的和利益驱动下,交际者大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设法完成任务(Jenkins et al.,2011;Mauranen,2012;Mackenzie,2014;Seidlhofer,2011)。BELF交际中的元语用话语体现出交际者在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Caffi,1994)的驱动下,对意义的表达与理解进行协调适应的意识和努力,应从个体认知和社会两方面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使用的动机与机制。
Kecskes(2007,2013,2017,2019)整合了社会与认知两个纬度,提出以社会—认知视角(socio-cognitive approach,SCA)研究语用问题,关注交际中个体认知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互动过程,特别是互动中的涌现特征,是21世纪语用学理论的*新发展。在SCA框架下,BELF交际中的元语用话语体现自我中心(即个人认知因素)与合作(即社会因素)的互动转化。BELF交际者为完成任务,基于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选择元语用话语激活相关语境因素,明示交际意图,使之变得凸显或更加凸显,建构涌现集体共知基础,引导与制约交际按期待的方式进行,旨在达成意义的共知和互解,完成交际任务。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建构BELF交际中元语用话语的功能发挥模式。该目标细分为以下四点:①描述BELF交际中元语用话语的语言表征特点、主要类型及使用频率;②在SCA框架下描述BELF交际的语境动态性及语境制约性;③调查在不同语境因素制约下,BELF交际者的认知心理状态,描述交际者自我中心与合作的动态转化过程;④在SCA框架下揭示BELF交际中元语用话语对交际协调适应的动机与机制。
本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点。
首先,增加对元语用意识在BELF交际中功能发挥的认识。以往元语用研究多专注单语、单文化(monocultural)环境,虽然也有个别学者探究跨文化语境下的元语用现象,但没有对BELF交际中元语用意识及其标示语的探究,本书进行的系列研究增加对元语用意识在BELF交际环境中功能发挥模式的认识。
其次,增加对BELF交际的非实体性特征的了解。BELF研究开始转向探讨交际的动态性、灵活性和相依性。本书在SCA框架下,揭示来自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如何选择元语用话语,包括元语用表达,相互协调适应,最终达成意义的表达与理解,增加对BELF交际的动态过程的了解。
再次,提高对BELF交际者跨文化和交互文化语用能力的认识。ELF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是英语使用的跨文化语用表现、跨文化语用交际能力及跨文化语用“无能”(冉永平,2013)。BELF交际中的元语用话语体现交际者的跨文化和交互文化语用能力,本书通过了解交际者如何使用元语用话语,寻求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协商空间,相互介入,协调适应,可以提高对BELF交际中跨文化和交互文化语用能力的认识。
最后,指导商务英语教学和商务实践活动,并对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作为商务通用语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BELF交际日益普遍,本书对其中元语用话语功能发挥模式的建构可以在实践上指导商务英语教学与实践活动,如商务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以及商务会议中的团结协作等。另外,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本书对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作为商务通用语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1.2 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简述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面对面互动的BELF交际中使用的元语用话语,包括元语用表达,具体指不同母语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在商务场合使用英语进行交流时选择的元语用话语或元语用表达。BELF交际的目的明确,合作共赢的意识较强,虽然交际者之间缺乏共有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但基于共同的目的和利益,交际者双方会选择元语用话语对交际进程和效果进行协调适应,设法完成交际任务。本书基于以上认识,观察和描写BELF交际中元语用话语,包括元语用表达的语言表征、类型,并在SCA框架下揭示这些语言手段对交际进行协调适应的动机与机制。
本书以SCA为理论基础,揭示BELF交际中元语用话语,包括元语用表达,所体现的对交际协调适应的动机与机制。SCA主张融合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考察交际过程中的合作与自我中心在交际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倾向性和程度。Kecskes(2010:60)指出,交际中,“合作是一种以关联为尺度、以意图为导向的交际实践,而自我中心所体现的是以凸显为尺度,以注意为导向的交际特征”。选择SCA作为本书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三点原因:①BELF交际关涉不同母语文化的交际者,SCA的提出为跨文化交际中语言使用提供解释与研究的视角以及分析的概念与框架,正契合本书的研究目标;②BELF交际过程的描述需要跨学科视角,而SCA整合交际所涉及的个体认知和社会因素,强调认知与社会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体现语言研究的跨学科视角;③探究BELF交际中元语用话语对交际协调适应的动机与机制需要采用动态交际观,分析交际中的动态涌现特征,而SCA区分前语境与现实情景、原意图与涌现意图、个人凸显与集体凸显等,并从自我中心和合作两方面论述它们之间的互动转化,在SCA下考察元语用话语的使用可以更清晰地揭示BELF的非实体性特征。
在SCA的理论框架下,BELF交际可分为两阶段:①交际初始,交际者(A和B)基于前语境,在最为凸显的知识或信息引导下,选择与当前情景语境最适切的意义交际,该过程体现了自我中心驱动;②交际进行中,交际者(A和B)的前语境、个人凸显义与当前情景语境互动,此时,交际者不能仅以自我为中心,在表达意图时要进行关联选择,注意涌现凸显义,当发现交际中出现问题或存在潜在问题时,选择元语用话语或元语用表达进行协调适应,努力寻求并建构涌现共知基础,确保交际按预期进行,如图1-1所示。
图1-1 SCA框架下BELF交际中的自我中心与合作
本书主要回答以下五个研究问题:①BELF交际中元语用话语的主要语言表征特点及其类型有哪些?②BELF交际中元语用话语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