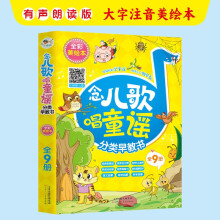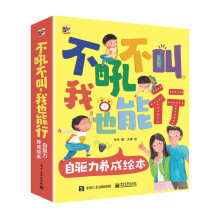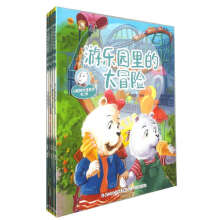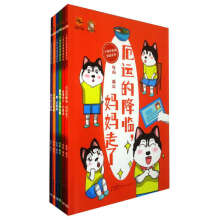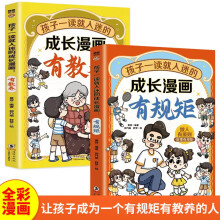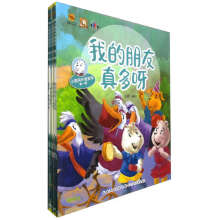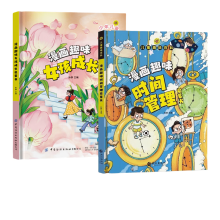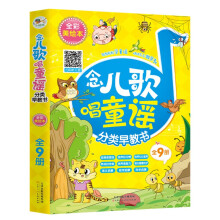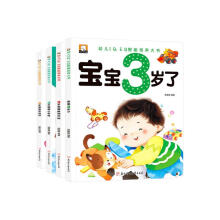“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一个小男孩在自家的庭院里倚着大石头,如痴如醉地读着《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用空城计智退司马懿的故事。合上书,他甚至能将故事背诵出来。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与英勇无双的关羽,都深深吸引着他。昨晚,他又读完一遍《水浒传》,小说里林冲、武松等绿林好汉也令他心仪万分。这个小男孩就是日后的国学大师钱穆。
钱穆先生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他七岁时进入家乡的私塾学习,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又勤奋刻苦,没过多久便能认很多生字,可以说是过目不忘。
到了十岁,钱穆进入小学学习。在那里,他遇到了许多令他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其中,他最爱读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文章,后来他又在老师的教授下学习了朱熹和王阳明的著作。因为阅读视野开阔,不受某一家、某一派的限制,所以思想受的拘束少。他在后来的治学中都是从典籍出发,实事求是,持论没有门户之见。
除了接受学校的教育外,钱穆受到的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他的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对教育有着独特的见解,对钱穆采取的是启发式教育方法。在钱穆九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父亲带着他参加朋友的聚会。父亲的朋友让他背诵《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他当即流利地背出,一字不落,令在场的大人们刮目相看,啧啧②称赞,他便有些得意。这一切都被父亲看在眼里。第二天,父亲带着钱穆外出的时候,路过一座桥,父亲便问他:“认识‘桥’字吗?”“认识。”钱穆自然认识,便脱口而出。父亲接着问:“‘桥’字何旁?”钱穆不明白父亲为何问如此简单的问题,但还是恭敬地答道:“‘木’字旁。”父亲再问:“‘木’字旁换了‘马’字旁,是何字?”钱穆开始觉得有些惶恐,答道:“‘骄’字。”父亲淡淡地说:“你昨晚的表现就像‘骄’字,你明白吗?”幼小的钱穆当即明白了父亲的用意,惭愧不已。钱穆先生晚年还回忆起这件事,说明父亲对他温和而又严格的教育使他印象深刻,这也为他日后虚心治学的态度打下了基础。
一个人长大后所做出的成就,与小时候所下的功夫是分不开的。钱穆童年时受到的家庭启蒙与国学教育,令他受益终身。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位“国学狂人”,他们是师徒关系,均学养深厚,桃李满天下,但性情狷介孤傲,人称“章黄”。章,就是章太炎:黄,则是国学大师、人称章门第一高足的黄侃。黄侃学问精深,诗文俱佳,可是脾气却怪得很。据说他当年在中央大学教书时,与校方约定“三不来”,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校方敬重其学养,听之任之。
神童
黄侃,字季刚,祖籍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音韵训诂学家。
黄侃自幼聪颖,七岁时代母给父亲写信要钱,附诗一首:“父作盐梅令(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当他的父亲读信时,一位老友恰好在场,读了此诗,大为赞赏,当即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黄侃。
九岁时,他已经是乡间有名的神童。父亲在信中告诫他:“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活天趣,亦不可忽。”意思是,你现在有着神童的美誉,这自然很好,但应该时时鞭策自己,不能被美誉冲昏了头脑。你应该像古人那样爱惜光阴,不要荒废时日,虽然现在还年少,但转瞬之间就长大、变老了。除了读经书,还可以写点诗文,激活一下天性趣味,这对于人生也是不可忽视的。黄侃牢记父亲教诲,勤奋读书,积淀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自成一家,同时创作了大量诗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读书
黄侃读书非常认真。每次读书之前,他都要记下开卷时间,读完再记下结束时间,这样按日计功,寒暑不辍,绝不半途而废。对于那种随便翻翻、读几篇就放弃的做法,他极为反感,斥之为“杀书头”。他的弟子、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回忆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黄侃认为:“书是给人读的,尽管在上面批写,不要把它奉为天神似的。”因此,黄侃凡读书一定会做圈点批注,往往一本书读完,全书已写满了批注,丹黄灿然,几乎没有白地儿。他在日记中曾经提到,自己平生读书圈点,《文选》大概十遍,《汉书》三遍,《说文解字》《尔雅》《广韵》已经不知道多少遍了。1935年,黄侃因病逝世。去世前,虽吐血数升,他仍然强支病躯,将一部书的最后一卷圈点完成。其读书用功之勤,可见一斑。P6-9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