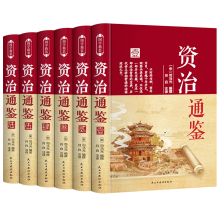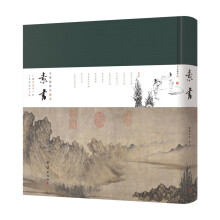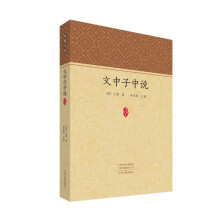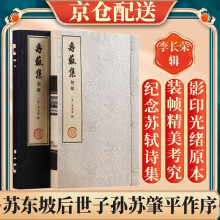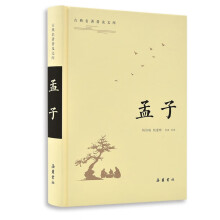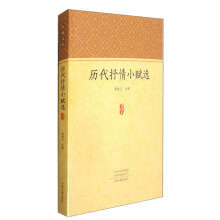張遠覽(一七二七—一八○三),字偉瞻,號桐岡,清河南省西華縣人。九歲而孤,刻苦讀書;二十歲時,成爲秀才。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中式舉人。此後,六次北上京師,參加會試,但均不售。以大挑,選正陽縣教諭。他任職期間,以古學課諸生,數年之間,士風爲之一振。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畢沅官河南巡撫,久聞大名,張遠覽因而被聘爲開封府教授。七年後,以卓異薦,選授貴州鎮遠縣知縣。張遠覽在鎮遠爲官期間,以德化民,多有惠政。一年後,題署黎平府下江通判,亦多善政。數月後,引疾求罷。離任之日,囊橐無餘。歸里後,與門人王耕畬講習,勤於著述。所著書有《詩小箋》、《春秋義略》、《春秋主臣録》、《古詩録》、《碑幢聞見録》、《書意》、《舊聞初存集》、《採薪集》、《古歡集》、《汝南集》、《黔游集》、《直方堂詩草》、《桐岡文存》等,多傳於世。
在學術上,張遠覽致力於經學研究,對《詩經》、《春秋》下過很深的功夫,著有《詩小箋》、《春秋義略》、《春秋主臣録》等,成績較大,正如吴德旋給他所作的傳記中言:“君與偃師武虚谷大令,並以經學著聲中州。”(吴德旋《偉瞻張君傳》)。乾嘉時期,在中州的經學研究領域,他與武億齊名。
張遠覽的詩文創作,多表彰鄉賢,如理鬯和、胡然、錢柳圃、王黄安、劉海鶴以及他的父親張華等,並序刻這些鄉中先賢的詩文集。他的古文創作,除詩文集序與壽序外,大部分是碑傳之作,風格近於歸有光,多叙寫鄉里先賢故舊,表彰貞烈,情感真摯,惻惻動人。在詩歌領域,張遠覽撰有《戲論明詩七首》,推許徐禎卿、李攀龍、陳子龍,貶斥薛蕙,認爲薛蕙的詩歌創作是繼承邵雍《擊壤集》的“俚詞讕語”。因此,他的詩歌書寫,比較近於前後七子。具體而言,他的詩歌創作,多古體詩,取法漢魏,措辭雅煉;而近體詩則師法杜甫,極少流連風物,多爲述懷紀事,偶見登臨之作。相比較而言,他在古文創作上的成就高於詩歌,這可能是他在詩歌創作上不是很用力的緣故。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西華縣署所刻《桐岡存稿》,爲張遠覽詩文集的唯一刻本。本次整理,即以此本爲底本標點而成。由於張遠覽的詩文只有這一刻本,所以,在校勘方面,即使偶有校勘,也是理校。凡底本缺字或字迹模糊不清的,一概用方框(□)替代。
限於整理者的腹笥與用力不夠,本書難免存在疏漏之處,希望讀者予以批評指正。
卷 首
卷首西華張桐岡先生,爲乾隆時名宿,文章學問,海内宗仰。青浦王述菴先生稱其沉靜誠慤,古文得震川一體,嘗采入《湖海文傳》。鄢陵蘇氏近有《中州文徵》之刻,亦采先生之文,顧未見其全集。歲乙酉,余承乏斯邑,訪先生之遺著,從其曾孫尚弼上舍得鈔本,《詩小箋》七卷,《春秋義略》十六卷,《初存集詩》一册,又得蕭步九秀才所録先生之文,並《文傳》、《文徵》所選,彙而得若干篇。既讀其門人王耕畲所爲先生墓誌,知此外著述尚夥,而得見者止此。余維先生與偃師武先生虚谷,並以經學著聲。虚谷《授堂集》久行於世,而先生竟無專集刊行。今之僅存者,又不免鈔胥譌脱。爰即前所彙者,詳加厘正,次爲文六卷,詩二卷,付諸剞劂,以廣其傳。其《詩小箋》、《春秋義略》,别謀校刻焉。中州爲人文淵藪,國朝之以文名家者,侯、宋、賈、李之倫,蔚爲一代耆碩。先生晚出而與之抗行,不可謂非健者。嘗攷先生鄉闈出朱石君先生門下,垂三十年,始爲令於黔之鎮遠。未幾,乞老以歸,讀書邑之城南。水田一區,老屋數楹,藏善本書二千卷。杜門却埽,怡然自足,固不僅以文章爲時稱説已也。今先生集出,前輩典型,珍若星鳳。庶幾是邦文獻,有所攷云。
光緒十有六年,歲次庚寅,秋九月,東臺鮑振鏞識。
張桐岡先生墓誌銘 同里王辰順撰
嘉慶八年冬十月癸亥,吾邑桐岡先生卒於家。辰順夙承函丈,一官匏繫,遽驚哲人之萎。嗚呼,安放矣!越明年,葬有日,嗣子居平持狀走宛,請辰順志先生墓,乃據狀書之。
先生姓張氏,諱遠覽,字偉瞻,號桐岡,世爲西華人。五世祖善政,萬曆己未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高祖印爌,生員;曾祖圻翰,康熙己卯武舉;祖文桂,康熙癸酉舉人;父華,辛卯庚子副榜,主一時壇坫,學者所稱醇民先生也。母姚氏。
先生九歲而孤,讀書日記數千言;弱冠,入郡庠,旋食餼。乾隆癸酉,以選貢入都,北平黄昆圃先生一見,甚器之。歲己卯,領鄉薦。六上公車,不售,以大挑,選正陽教諭。課諸生,敦行學古,數年之間,士風大振。時畢秋帆中丞撫豫省,夙稔先生名,檄攝開封府教授,兼以書幣,屬令促裝。及至,以金石文字相質,贈金百兩,緞四疋,先生受緞反金,强之,終不受。壬子,選貴州鎮遠縣知縣。鎮遠,當南北水陸衝衢,俗尚奢靡。先生到官,日飭内外,書役皆衣布,非紳士不得衣帛。富商有執贄請見者,諭以安分守法,勿以厚貲結納官長。縣舊事:每逢元旦、上元,署内外綵桐氊地,籠燈以千計,皆四鄉居民供給,先生盡革之。在官僅一載,題署黎平府下江通判。下江苗民雜處,梗頑難化。先生至,訟庭日閒。居三月,上官委以鉛差,差竣,許以知府題署。先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乃引疾求罷去。去之日,囊橐無餘,賴黔陽令姚文起資之,始得旋里。
先生性至孝,遇先人忌日,涕泣不食,曰:“此終身之喪也。”官正陽時,兄漁莊先生無子,迎養任所。卒,則請假上官,要絰扶櫬歸葬。平生寡交遊,交則情誼篤至。同里周仲遠赴禮闈試,至彰儀門外病卒。先生聞訃,親視含殮,約同鄉士大夫賻之,徒步二千里,以其喪歸。尤喜表揚前賢,自父醇民先生《抱影盧詩》刻外,如胡湄園、理寒石、劉海鶴、王聖能、錢柳圃諸先生詩文集,皆序刻而傳之。先生沉酣經史,旁及百家,善屬文,尤工詩,日與學者講授,樂此不疲。所著書有《詩小箋》、《春秋義略》、《春秋主臣録》、《古詩録》、《碑幢聞見録》、《書意》、《舊聞初存集》、《採薪集》、《古歡集》、《汝南集》、《黔游集》、《直方堂詩草》、《桐岡文存》若干卷。一生持禮甚嚴,雖盛暑未嘗見體。易簣之夕,諸門人咸侍側,曰:“正吾首與手足,整吾衣冠。”召家人,遍視一周,含笑而逝。距生於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享壽七十有七。元配王安人,繼劉安人。其閫範懿德,詳先生所自爲兩安人狀中。側室颜孺人,前先生六日卒。子男三:長居燮,太學生,早卒,王安人出;次居庶,嗣世父;次居平,颜孺人出。女一,歸生員丁瑞玉。孫男一,念之,早卒;孫女一。今卜於三月初八日,葬先生於城東南新阡,以王、劉兩安人暨颜孺人祔,禮也。銘曰:
於維先生,命世矯矯。堂名直方,德爲坊表。綽有至情,篤於人倫。便便腹笥,力追古人。經術湛深,管豈窺豹?叩之則鳴,用之則效。廉吏可爲,所至有聲。黔遊匪偶,甘棠敷榮。出入里門,敬而無失。全受全歸,始終如一。修名允立,本自家風。子子孫孫,視此良弓。
偉瞻張君傳 宜興吴德旋撰
偉瞻張君,諱遠覽,河南陳州府西華縣人。幼孤,能自力於學。性敏慧,讀書日記誦數千言。事母盡孝,家雖貧,竭力營甘旨無缺。母卒,哀毁甚。及葬,廬墓三年。
君博學,工爲文。乾隆癸酉,充拔貢生。己卯,本省鄉試,中式舉人,選授正陽縣學教諭。其教人,先器識而後文藝,遠近爭來就學,庠舍至不能容。其弟子經指授爲文,用君説,成進士,膺鄉舉者甚衆。巡撫畢公嘉其能,以卓異薦,選授貴州鎮遠縣知縣。青浦王述菴侍郎爲叙以送之,謂君用博雅之學,播循良之治,必能寬猛以時,使民苗咸輯也。及君涖任,果如所期焉。鎮遠,古夜郎地,苗民雜處,獷悍難治。君結以恩信,皆帖服,遵約束。舊俗:子女多者,其父母往往忍不舉。君出教諄諄然,論以義理,苗民感動。甫七月,而舊俗爲之一變。大吏以爲能,令署黎平府下江清軍理苗通判。下江,環治皆山,以山爲城,缺處補之,以甎價十倍於石。君以爲勞民傷財,無益也,以石易之,歲省工價無算。下江山中,故有虎患。君至,則出多貲,製火器,率武弁鄧元第等往山中,日習之,下江由此無虎跡,苗民賴之以安。君之在下江甫四月,因疾致仕歸。歸日,苗民扶老攜幼,涕泣相送。
君既歸西華,而西華民束玉林者,潛謀不軌,跡且露,君與邑大夫密謀擒治之;又恐其黨之潜入城中也,力疾躬率門人子弟輩晝夜巡察。君雖以老疾家居,然遇事猶奮發有爲如此。若其他爲善於鄉,而鄉里戴其德者,皆常事,故不書。所著有《詩小箋》、《春秋義略》、詩集、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
吴德旋曰:君與偃師武虚谷大令,並以經學著聲中州,後並爲循吏,然皆未竟其用。而儒者之效,不獲大彰顯於世,惜哉!余之聞君名也,由新城陳碩士侍郎。凡君所著述,悉以視余,余得而讀之,因次其傳。
桐岡存稿卷第一 文一
褚遂良論
唐褚遂良,賢者也,以忠見逐;劉洎,賢者也,以忠見殺。世言洎之死,遂良譖之也。張子曰:嗚乎!吾悲夫與日月齊光者之蒙惡於千載,曖曖焉而莫之雪也。夫賢者,有殺人,無譖人。洎之受詔,輔太子監國也,對太宗曰:“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此言所以見殺也。蓋太宗積欲殺之,大臣亦積欲殺之,是必有希帝旨、阿大臣意而入譖。大凡人之譖人,有所阿於人,有所利於己。譖人不死,譖不止。當魏王泰、吴王恪之時,褚公不阿太宗;高宗之初,不阿武后以譖王后。前後與褚公同執政者,岑文本、馬周、劉洎、韓瑗、來濟。以爲妒賢邪?諸公固皆賢者也。以爲惡逼邪?諸公固皆執政者也。不譖岑、韓、馬、來,而獨譖劉,於人焉阿?於己焉利?當其還笏流血,止知不負先帝之託,其他利害生死,皆置度外,天地感而鬼神泣矣!險賊陰毒,譖人於死,非豺虎不食者不爲,而猥曰忘身奉上之賢實爲之,其不然也決矣!然則曰褚遂良譖劉洎者,何也?曰:此許敬宗爲之也。敬宗以己所優者加於己所深忌之人,而遂以受此曖曖於千載也。許敬宗之傳曰:《太宗實録》,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將半,專出己私。計無有急於誣褚公者,誣褚公於太宗之時;計無有以殺劉洎事加之者,故曰:褚遂良譖死劉洎者,許敬宗之言也。許敬宗之急於誣褚公者,何也?蓋貞觀之世,房、杜、王、魏同德相濟,敬宗無所容其姦。自以爲當武德時,己在十八學士之列,褚公之父亮,其同官也。褚公以魏鄭公之薦,一旦大用,位出其上,受遺詔託孤,而且直諒多聞,朝野同仰,已屬深忌;又房、魏諸公以次彫喪,己可以肆其所爲,敏達可以服衆心,辯折可以關多口。自度獨不可以欺遂良,遂良一日不死,敬宗一日不安。潭州有行,不三年而褚公卒矣!敬宗乃訑然坐政事堂,逐韓瑗、來濟,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如反掌。劉洎不殺於貞觀之時,必殺於敬宗之手,乃稔毒逞穢十有餘年,日夜以思,恐天下皆思褚公之忠,而憐其逐。將使天下疑其忠,而不憐其逐,則莫若誣以已往不可覆按之事。以爲洎固表表名臣,誣以洎事,則尤爲人所深惡。雖其讜言勁節,昭然耳目,而陰竄此一事,則他美不足掩其惡,且有此惡,即其美亦非真美。於是筆之曰:洎與遂良不相中。即誣奏洎,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又念無忌者,國元舅,致之死,宜可憂,莫若誣其害國懿親之可以解免。於是筆之曰: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有宿怨,誣與房遺愛善,流象州;吴王恪,無忌所忌,坐以遺愛事殺之。當其時,褚公之子弟及長孫氏皆投荒禁錮,無在朝者,而李義甫、王德儉、崔義元、袁公瑜、侯善果之類,布滿臺省,誰過而問之者?嗚呼!殺正人於方剛,汙忠魂於既死。潛煽毒於已往,巧售欺於將來。此其所以爲許敬宗也。修史者既知其改竄《實録》,而第曰盛誣封德彝,虚立錢九隴功狀。以太宗賜無忌《威鳳賦》爲賜尉遲敬德;龐孝泰爲高麗所襲破,而曰屢破賊。明其細而莫發其鉅,於長孫無忌、褚遂良傳不言劉洎及二王事,若爲賢者諱然。顧曰: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嗚呼!其亦爲許敬宗所愚而未之思也。或曰:洎死既不由褚公,史稱洎子宏業顯慶中訴遂良譖死狀,李林甫右之,是亦不足信歟?曰:其訴也,其右也,皆敬宗使之也。既竄其事於史,復暴其事於朝,此尤易洞其隱也。或曰:褚公譖劉公,安知不有其端倪,而奈何決之以必無?曰:事之然否,不據人之生平以爲斷,則齊光於日月者,不難使之慘甚於蝮蜮;誣人者必誣人以必不爲之事,而其誣乃爲得力。所謂點白爲黑者也。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豈有不利之端倪也哉!許由椎埋,黔婁行刦,屈原媚鄭袖,陶潜臣劉裕,褚遂良譖劉洎。采蓮采蓮,首陽之巔。惟其不然,猶曰或然。嗚呼,悲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