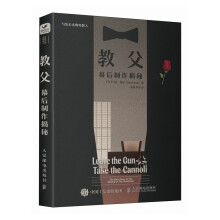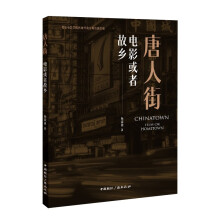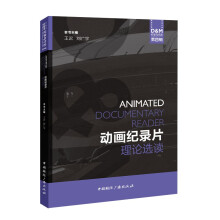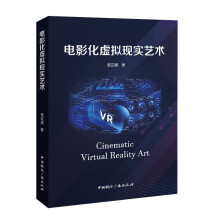《中观视域下的形式本体与认知建构: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诗学研究》:
一、认知理论概述
首先,认知理论不是一种专门的电影理论。认知主义不是传统电影理论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更倾向于一种研究立场与态度。认知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认知主义应被视为“一种富有特征的姿态”,它“通过诉诸内心的表达过程、自然过程和(某种意义上的)理性的中介,力图去解释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行动”;①它不是一个单一性的理论,而是在认知主义大旗下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究的探究努力,“认知理论家普遍认为,认知主义最好被视为一种‘角度’(perspective)而不是一种‘理论’,在这种角度之下,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甚至彼此冲突的理论”①,是众多理论的集合体;它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思考论题不完全相同;同样,也不使用统一性的整体性理论来指导这些领域的工作,不存在公认的“认知主义”纲领或者原则。在他们看来,这也正是认知理论区别于宏大理论的地方——认知主义是从面对具体问题出发以寻找、确定合适的认知理论模式来使用,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的“大师叙事”式的自我指涉论证。
其次,认知主义将研究焦点集中在与人感认知对应的电影形式要素上,以认知模型来处理相关问题,并对有限的问题提供明确的解释,而不是把电影视为语言的一种“类比”。认知理论是伴随认知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影研究方法与路径,它不完全局限于认知科学的范围之中,但在基础逻辑层面明显受其影响。“认知科学主要是研究智能问题的解决程序或信息处理过程,它使用电脑作为人脑的一个隐喻。尽管认知主义者早已把‘电脑隐喻’抛诸脑后,但他们仍然在使用理性模式和实际问题解决模式处理叙事理解和感知中的某些因素”②;他们不把电影当成是语言的类比,而是倾向于认为,认知主义又回到了麦茨创立第一符号学的起点,即重新思考“电影是如何被理解的”问题,只不过他们是使用认知模型来思考,而不是电影的语言符号模型;认知主义也不完全排斥精神分析,但认为其作用仅限于特定某些方面(情感的和非理性的)。认知主义的电影研究绕开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引用“感知理论”“推理理论”“信息处理理论”来理解电影在因果叙事、时空关系等方面是如何被接受和领会的①,因此,认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可控范围内而进行的观众能动性研究。它向科学方法靠拢并以提供具体的解释为目标,是与中观研究密切联系的。
再者,认知主义研究赋予了观众充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强调在意义制造过程(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观影过程)中认知的普遍性和共通性。罗伯特·斯坦姆总结道:“大部分的认知主义者都会同意:(1)电影观众,最好被理解为有理性,并企图透过文本资料,了解事实或叙事的意义;以及(2)这些过程,跟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意义制造过程,没什么两样”②;不难发现,在电影的认知研究者那里,观影体验同日常生活有着同样的认知基础,认知因此是探讨影片接受的重要角度;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参与了影片的理解、认知过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