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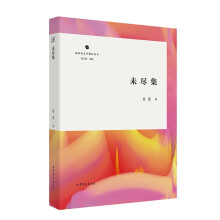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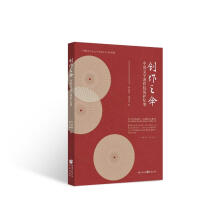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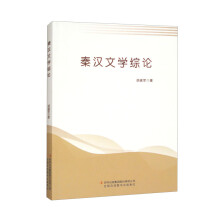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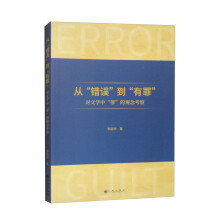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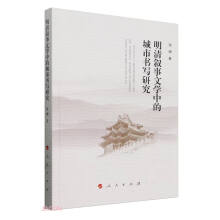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平民意识倾向,这表明中国文人从传统向现代意识的转型已基本完成。中国文学可以说从宋代以后就逐渐开始了向平民文化的靠拢,而这一现象是伴随着城市和市民文化的形成而缓慢形成的。所以,平民意识的形成是与市民阶层的出现相伴随的,使传统文人士大夫意识逐渐消解,最终在近代西学东渐和以下层社会为启蒙目的的“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从渐变到裂变的过程。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15年在《新青年》诞生以后,以《新青年》为先锋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无论是思想、文化、文学等都发生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与嬗变。但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这一变化过程,尤其是文学,最早从宋代以来的发展中就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而到了晚明时则就显示出其寻求突破的明显痕迹。关于这一论述,我在《新文化与新文学——基于晚明至五四时期的文学文化转型研究》一书中有较为详尽的分析,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总体而言,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为何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而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化与文学又似乎如此稳固不变,即使变化,也是在传统体制内做一些小的变革与修改,没有发生实质上的转换,我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儒家文化本身就有着许多精辟的观点与认识,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它对中国文化的长期稳固性有着良好的黏固作用,其次是儒家的“仁爱”精神所产生的对人的“关怀”内核,是其能够长期存在的基础。所以即使一个朝代的矛盾发展到无法解决的时候,人们也会普遍认为,那是因为当朝的思想精神已经背离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所以往往就会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缓解矛盾,从而唤起人们对新的王朝的希望,这样中国文化就走了一条不断循环的道路;而这一模式,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看,可以说是一贴灵丹妙药,万变不离其宗。当每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之初,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其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调整。譬如就文学而言,唐朝的诗歌,在业已形成的比较完善的古诗基础上,逐渐使诗的形式走向完善,建立起完美的“格律诗”;到了宋代,唐诗所建立的诗歌形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后人即使想超越,其实都是很难的,所以文学就会伴随当时的文化调整而发生变化。宋词的产生,其实是与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思想意识密切联系的产物,当宋朝都市与商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之时,与其相适应的宋话本的出现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由此看来,中国文学到元有散曲与杂剧,明清有小说,都是如此逻辑发展的结果。在五四时期,胡适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显然,胡适先生的观点是基于20世纪初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日益发生影响的背景所说的,目的是为了给“白话文”的合理性寻求理论支撑。其实,就中国文学而言,不是简单地能从进化论的理论解决问题的。因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其有效性是建立在没有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意外事件的基础上的。19世纪中叶以来,晚清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或者说意外事件,事实上已经不是能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控制,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天秤已经倾斜,即使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洋务运动”甚至是“维新变法运动”,其实“维新运动”已经包含着一些新的思想,也只是晚清的垂死挣扎,由于历史意外事件的发生,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自身发展的步伐突然不再有效,而是酝酿着巨大的爆发力量,它改变了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轨迹,这就是以启蒙为背景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
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形成,可以说是从晚明以来几种力量所形成的合力,无论是晚明的启蒙思潮,还是晚清的维新运动,其实只是中国文化与文学内部自身力量的积聚,但历史进入19世纪以来,曾经被我们认为是“夷狄”的西方文化却使我们“文明古国”的优越性荡然无存。正像鲁迅所说,“嗟乎,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则取以供览古之人,使摩挲咏叹而外,更何物及其子孙?否亦仅自语其前此光荣,即以形迩来之寂寞,反不如新起之邦,纵文化未昌,而大有望于方来之足致敬也。故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而近代改革思想家王韬也说:“自世有内外华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之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积以薄人哉?”王韬:《华夷之辩》,见《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7页。我们可以看出,在晚清无论王韬,还是鲁迅,这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文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用一种国际化的眼光来考察,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文人思想明显地在逐渐消解,所以无论是对中国的文化还是文学,认识上均产生了质的变化,尽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那时还没有盛行,但说明正在积蓄着能量,等待时机,一触即发,体现了中国近代从渐变到裂变的过程,而渐变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裂变则来得如此迅猛。从《新青年》诞生到20世纪20年代初,短短几年就“涅槃更生”,无论是文化思想还是文学思想和文学形式上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型,因为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外来思想跟晚明以来直至五四中国文人业已形成的思想潮流相结合,发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促使旧文化与旧文学迅速解体,中国文化和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重构阶段。文化上步入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轨道,而文学上则突破了旧文学的“文以载道”思想,代之而起的是用文学诠释新文化与新思想;语言上则走向“文言一致”,表现上则像郭沫若所说的“绝端自主,绝端自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大约从一七零零年起始,到一九零零年止,在这期间,文学的方向和以前又恰恰相反,但民国以来的文学运动,却又是这反动力量所激起的反动。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不看清楚清代文学的情形,则新文学运动所以起来的原因也将弄不清楚,要说明也将没有依据。”周作人先生的这一观点,如果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其合理性。因为从逻辑上看,文化与文学的变化,不可能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它一定是多种力量共同完成的。如果没有晚明以来中国文化自身在不断寻求突破,仅仅依靠外来因素,那是说不通的;但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单纯依靠自身因素,变化也是十分艰难的。正是在适当的时间,两种文化里的某种因素相碰撞,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产生的深层原因。那么,外来文化中哪些因素是产生新文化的构成因素呢?我认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在近代经历了这么几个过程,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无疑是具有近代性质的大量报刊的产生,即大量具有近代意义的传播媒介产生并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与观念是推进中国外化与文学转型的重要因素。
中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晚清报刊大规模产生的推波助澜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转型。而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特别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是一个渐次变化的过程)。首先是由于西人在华创办报刊,通过报刊媒介把西方近代思想与观念传播到中国,使中国有先知先觉思想的一部分文人逐渐与传统文人的思想观念相比发生着些微的变化。如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鸦片战争后的魏源等,先后开启了文人对传统社会与国家问题的思考,迫使中国文人改变原来唯我独尊的思想,主动对中国传统思想认识作相应调整,这也是产生19世纪末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在晚清报刊的影响下,思想观念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文学观念相应的变革。文学变革在近代史上的变化过程的渐次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文学观念的变化(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为代表),之后文学所发生的变化就是为了适应文学观念变化与内容的变化,随之是为表达新思想内容而产生的文体形式的变化。所以能够产生晚清文学史上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的结果,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具体而言,“小说界革命”不仅是要求通俗化,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观念的革新,由此带来的文学语言上的变化;而内容上也由传统小说中人物塑造的“英雄化”走向平民化,浪漫化走向现实化。“诗界革命”也不单纯是要求口语化和简单的通俗化,而是注重诗歌反映内容的扩大化与时代性。所以新的意象、新的名词出现在近代诗歌中也是必然的趋势。“文界革命”也不仅仅是体现在新文体上,更为重要的是其作者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认识的变化促进了多元化的文学与思想表现;它不是一味循规蹈矩,而是文体根据作者的感情变化而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不受前人束缚,这些特点是符合近现代文学转型特点的,而且也是符合晚清报刊体文章的风格特点的。所以“新文体”不单纯是借鉴其他外来文学的一种全新的文章表现形式,更是在吸收融合了晚清报刊体文章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
我们有理由相信晚清报刊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其所传播的新的思想观念及其不拘一格的自由而不受任何束缚的文章写作风格与文章反映事实的真实性(这对后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不是文学的本体。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正是在新的思想观念推动下,文学本体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所以在20世纪初,诞生了大量的文学刊物,随后又诞生了许多报纸副刊(阿英先生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已经作过详尽阐释,在此不再赘述)就是例证。在当时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主要有1902年的《新小说》、1903年的《绣像小说》、1906年的《月月小说》、1907年的《小说林》,它们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近代转型。而1897年,作为《字林沪报》初具副刊性质的“消闲报”的产生,其实已说明了报刊向娱乐化的转变(尽管梁启超更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但文学的娱乐化已成为时代的趋势,因为娱乐使文学更接近其本质)。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学的娱乐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平民化、通俗化与大众化。而到了20世纪初以后,文人意识的平民化,平民对文化共享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促使文人在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贵族意识,开始向大众转型。而这种思潮的形成,与晚清报刊所传播的西方近代思想观念是密不可分的。这一变化所产生的近现代文学其实与传统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文学的本质特点是“寓乐于教”,而近现代文学的整体趋势是“寓教于乐”。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正是在文学趋于娱乐化的背景下文学观念的转型促进了晚清近代文学的繁荣,而新的思想又通过娱乐的文学形式影响到广大的平民阶层,新思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追随。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报刊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文学表现内容与形式上的不断花样翻新,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文学自身的变革,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审美趣味,无论是从文学的语言还是文体结构或是文学内容都在推出新的变化,由此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逐渐转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的根本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出了不得不改的历史条件。
我们纵观晚清及近代报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基本线路图是非常清晰的:由思想观念的转变到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自身的转变。从19世纪初由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苏门答腊岛创办)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办报刊,其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而非是本体的,主要产生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上的影响,而到了后维新的20世纪初,则开始倾向于文学自身文体形式的变革,所以在20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中国文学发生转向已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的潮流。
所以20世纪的中国文学,正是晚清以来思想潮流转型的结果,文化的转型同时带来的是文学潮流的转型,而中国文学在20世纪转型的大致路线是:在人物的塑造上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英雄化人物到平凡人物的发展趋向,作品呈现出不同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无论是20年代的鲁迅、朱自清、庐隐、徐志摩,还是30年代的巴金,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诗人穆旦,都唱出了不同时代音符的交响,表现出不同时代的潮流与个体特殊性的追求与融合,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和文学本质的不同,文人意识与文学思想发生着深刻嬗变,它们是20世纪中国文化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引言
第一章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与平民意识的形成
(一)城市文化的形成是文人化意识消解的基础
(二)明末清初商业文化的兴起与小说的繁荣
第二章“救亡图存”话语政治背景下的矛盾抉择
(一)西学东渐的曲折之路
(二)盛世危言中的希望
(三)含苞待放的前夜
第三章中国现代文学的萌动——世纪之交的文学革新运动
(一)近代文人从“士大夫”意识到“平民”文学意识的
转型
(二)严复与林纾的翻译——近代翻译史的高潮
第四章启蒙文化语境中的“五四”知识分子
(一)筚路蓝缕的现代勇士
(二)稳中求变的理性智者
(三)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想转型
(四)从“五四”小说看作家创作理念的变化
(五)从文学观转型看现代作家创作心态
(六)带来新世纪曙光的前驱
第五章用文学诠释新思想的中国现代文学
(一)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
(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三)鲁迅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四)不同音符的时代交响
(五)“后五四”知识阶层的诞生与文学转向
(六)四十年代文学创作中的新潮流
参考文献
再版后记
温馨提示:请使用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