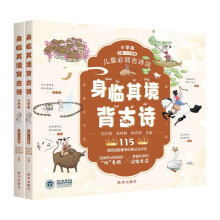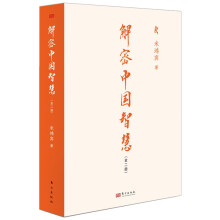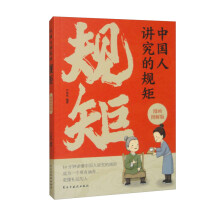《李光地研究》:
道家之学,起源于黄帝,集成于老聃。老聃(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世界文化巨人。他的传世之作《道德经》,其精华之处,闪烁着朴素的辩证法。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首次提出“道”的核心思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无为”之说,并非主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而是强调“道”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运用,既是不妄为、不强为,又是无不为,概括了当时“无为而治”与“依道治国”的方略。
李光地信奉此“道”,身体力行,在辅助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统一中国,整顿吏治、举贤惩贪,疏治三河(漳河、子牙河、永定河),废除圈地,直面储君风波、吸纳西学等棘手难题方面,胸无芥蒂,言行举止充分体现了正确审时度势,既不妄为、不强为,又无所不为,为创建康熙盛世,竭尽了股肱之力。
例如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年)夏五月,李光地请假回安溪湖头探亲,“道闻尚可喜请撤藩觐京,吴三桂、耿精忠继之。廷议悉如其请”。他就预料:“这三藩旦夕可能叛变。”等他到了家乡,果然耿精忠反形渐露。浙闽总督范承谟是一位忠义之人。李光地赶紧写了密信给范总督,建议他以阅操闽安为名,整师出城,疾走洪塘,溯流而上,直趋延平,控其上游,防范耿乱。
耿精忠“既蓄异志,思收罗才杰之士”。听说李光地回籍,“再四以王谕”召见李光地。李光地“虽知变在旦夕,然迹未彰灼。辞不获已,乃赴省一见,辄告归。”耿精忠不准李光地辞行。李光地假以父病危,“书泣请于耿逆,始幸见许”,逃离福州。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三逆果皆叛”。面对耿精忠叛乱和郑经(锦)烧杀,李光地“奉两亲遁匿荒谷,合门野服深匿”。郑经派与李光地熟识的杨芳,“前后三至”安溪游说李光地一起反清复明。李光地洞察到他们包藏着分疆裂土、祸国殃民的狼子野心,“以死拒之”。
康熙十四年(1675年)夏,李光地分析福建局势,为了秘密送出平乱的《蜡丸疏》,并“请大师入闽,禁屠戮,以慰残黎”,“惟谋于叔父白轩”。白轩问李光地:“必欲上密本何意?一泄大祸立至。”李光地向六叔解释此举虽冒死而行,却可望避免闽地长期战乱、生灵涂炭及覆宗之祸。白轩乃行,护送割腿藏《蜡丸疏》的家仆夏泽出汀州关,从江西辗转抵京。康亲王奉旨依计平乱。许多史实无不尽显李光地为了社会稳定、百姓安宁,善于“无为而无不为”,主动应变,不与耿乱同流合污,其用心何其良苦!
又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李光地服孝期满,赴京上任,抓住台湾郑氏政权内乱之机,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向康熙皇帝奏明:“郑锦(经)已死,子克塽幼,部下争权,宜急取之。”并以自身和阖族生命,力荐、担保施琅率师征台,独言可平。这除了再次体现他敢于为国一统之担当以外,还彰显他多谋善断。此大智大勇,稳操胜券,或许源于相生相克的道家思想。这从李光地为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撰写的墓志铭中可得佐证。他在此墓志铭中评论应对清初闽乱计策时写道:“吾闻攻毒之饵,恒出于瘴疠之区;乱之兴也,其受乱之地必有人焉。足以还自救也。”对此,吴幼雄教授的专题论述精辟翔实,令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当年,康熙皇帝对让谁率师平台心存疑虑,李光地就上奏说:“计量起来,还是施琅。他全家被海上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勇之夫;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气先夺矣。”为施琅最终获得专征权、一举平台创造了先机。
自古知兵非好战。李光地既敢为又不妄为,在平台以后,李光地应邀为施琅撰写的《靖海纪事》作序时,特别沉重地写下了一笔:“耀兵之非得已!”不忘宣传“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道家理念①。这无异于语重心长地提醒后人:千万要尽力避免像当年上万尸体血染海峡的历史悲剧重演!李光地在《榕村文集卷一·治》中评古论今时,也宣扬这个道家理念,赞同“以兵为凶事,故畜(古同蓄)而不轻于用,用而不究其武”的大智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