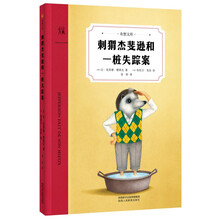春暖社饭香
早春的阳光明媚又神奇。它让河边的垂柳长出嫩芽,山坡上的野樱桃开满轻盈曼妙的花,就连无人照看的田野,也长满郁郁葱葱的鸭脚板、车前草、野胡葱,以及随处可见的水蒿菜。
野草似的水蒿菜,模样寻常,却是我们西郊人的最爱。这样的季节,掐一背篓带回家,和上几斤优质的稻米,年前刚熏好的腊肉,做成一锅香喷喷的社饭,就是一道令西郊人引以为豪的美食。
春天里,哪怕是最不讲究的人家,也会挑个晴朗的日子,做一顿温香软糯的社饭。否则,这家的大人、小孩都会觉得这个春天少了些什么。
土坎边,菜地里的水蒿菜刚冒出头,正伸展着娇嫩的身姿,打算趁着春风,长长个儿,婆就划算着给一家人做社饭。
婆去郊外打水蒿菜,总会带上我和妹妹,婆说小孩子眼尖,才长出来的嫩水蒿菜再小,也会被娃娃们发现。
有过跟爷爷采药的经历,我和妹妹认识很多植物。地枇杷、车前草、三月泡、白蒿菜和水蒿菜……白蒿菜和水蒿菜模样很相似,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能一眼看出它们的区别。白蒿菜的背面有一层韧性很足的白色薄膜,最合适做蒿菜粑。水蒿菜的菜叶水分多,因此做社饭之前必须焙干。
正是早春,白蒿菜还没长起来,见到的都是水蒿菜。还没到中午,我和妹妹的小背篓就装满了,婆的大背篓也装满了,我们相互打趣,又互相帮扶着回家了。
清洗、剁碎、焙干,碧绿的水蒿菜经过几个程序后,变成细碎的黑色的干燥粉末,样子有些难看。不过不用担心,它们在婆的一双巧手下又会焕发出另一番生机。
母亲取下挂在炕上的腊肉,在水里泡一阵,用小刀刮掉外面的黑色烟灰,再烧一锅热水清洗,直到黑魃魃的腊肉变得黄鲜鲜、油亮亮。婆把整块的腊肉切成方正的小颗粒,盛在细篾撮箕里。父亲在一旁劈柴、生火。我和妹妹也没闲着,清除野胡葱上的枯叶,剪掉根上的胡须。把从菜地里拔来的大蒜洗净、切碎,和胡葱拌在一起。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做社饭。
“加柴,烧大火。”婆右手握着大锅铲,左手叉着腰指挥灶门口烧火的爷爷。她那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气势,仿佛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爷爷把火烧得旺,整个厨房暖烘烘的,全家人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水开了,拿米过来,快!”父亲力气大,一撮箕浸泡好的白米端上来,婆抓起几粒米放在嘴里嚼了嚼,然后点点头,说了一个字:“倒”。
倒米不是毛手毛脚“哗”的一下子全倒进锅,而是要配合婆搅动锅铲的动作一点一点慢慢倒。
白色的大米跃进滚开的水里,沉到锅底。婆操起长锅铲,在锅底捞,这一捞,白米纷纷漾起来,仿佛在沸水里舞蹈。婆说,只有这样,煮出来的米饭才香。
所有的白米都进了锅,婆不再搅动锅铲,而是盖上大锅盖,让它们在锅里安静地躺着。几分钟之后,打开锅盖,此时,锅里的水已经收干,白米稍稍胀起。婆让母亲把事先准备的食材统统倒进锅,又加上盐。一下子,锅里可热闹啦:晶莹透亮的肥腊肉、鲜红精致的瘦腊肉、焙干水分的黑色蒿菜粉末、香味浓烈的胡葱大蒜……婆把它们和白米饭均匀地拌在一起。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