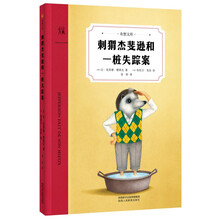三舅
我和三舅同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年龄相差不多,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说,无事不做。少年时的寒假,最盼望的是去姥姥家,觉得假期只有在那儿度过才算放假。随着期末考试的临近,我又开始思念起山区小镇了。
来到姥姥家的第一夜睡得不好,一铺大炕上睡的人一个挨一个。我睡觉时挨着三舅,还常常半夜起来,趴在结霜的窗玻璃上,看着漆黑的外面。北风咆哮,想把夜撕成碎片,我蜷缩在被窝里蒙住头,害怕玻璃让风挤成碎末,酿成一场灾难。狂风过后,往往飘起雪,这是我所期望的。
风刮得玻璃哐哨作响,后半夜就变得不那么猖狂。可我没有一点睡意,三舅躺在我的身边睡得香甜,对于我的举动一点都不知道。长夜中的风暴,打不断他的睡梦,我想叫醒他说一会话,便把双脚伸进他的被窝。
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许多家庭怕冻坏鸡呀狗呀,于是将它们圈进屋子里。姥姥家鸡笼子在屋地的一角,清晨公鸡精神抖擞,引颈高啼,引来同伴的咕咕声,一声啼叫在不大的空间回响,宣布新一天的到来。鸡笼子是木条钉成的,细铁丝吊挂着鸡食槽子,由于气味重,每天必须打扫,所以鸡笼子四腿脱离地面,在笼子下面铺垫上炭灰,这样清理起来方便。姥姥有个习惯,起来后会先卷一袋烟抽。咳嗽声中,打开老旧的台式收音机,从电流声到第五套广播体操,她不管别人醒没醒,天天如此,姨舅们已经适应。我爬起来,光着膀子跑到窗前,嘴贴着结霜的玻璃撮成圆形,哈出一团热气。不一会儿,玻璃上化出五分硬币大的洞,我眯缝着左眼向外望,窗外雪下得好大。
早饭匆忙吃完,三舅便忙碌起来,在我的棉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一种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也作□□)里,垫上捶软的乌拉草,然后找了一根绿皮电线扎在我的腰间,这样冷风灌不进衣服里。穿好衣服,戴上棉手捂子,我们在门斗的墙上,摘下挂着的爬犁。屋檐垂着钟乳石形状的冰溜子,褪色的红瓦上落满雪,我们推开门走进雪地。
爬犁拖得飞快,若不快跑两步,爬犁就会撞在后腿上。雪地上留下痕迹,我和三舅欢快地喊着,喊叫声在下雪后的天空回荡,我们踏过去,雪嘎吱嘎吱地响,我们向小河方向跑,爬犁左右摆动。我干脆坐在三舅的爬犁上,让他拉着我的爬犁,三舅把绳子搭过肩头,双手拽着爬犁,速度明显减慢。
小河披上洁白的大氅,清澈的溪水被冰冻的雪封盖。爬犁滑过河面,干枯的野草茎在雪中孤独地站立。过了小河就要上坡,三舅费力地拽着爬犁,嘴里喘出的气化为白色的云雾。我跳下爬犁,爬犁和脚印在雪地留下一串符号。
山坡陡斜,约有一千多米长,很少有车辆过往,三舅和伙伴们常在坡道上放爬犁。爬犁跑起来,坐在靠前的位置危险,要不时地把握方向,身体还要挡住扑来的寒风和粗硬的雪粉。三舅坐在前面我才有了安全感,他绷直腿,脚后跟蹬在雪中,爬犁绳从双腿间穿过。我在三舅的身后,把爬犁绳拴在三舅的爬犁上,然后搂紧他的腰。我做好准备说:“准备好了,火车开动。”我学着火车的汽笛声——呜!三舅松开脚,爬犁启动加速,借助下冲的惯性滑动,溅起的雪花四处飞扬,爬犁在雪花中越滑越快,惊险的快感,引得我们大叫。
大姐姓方,我家的邻居,她管我母亲叫高婶。我在家中排行老大,很希望有个可以呵护我的姐姐。
大姐年龄比我大十几岁,一天到晚笑呵呵的,她身上看不见愁事,任何时候一双大眼睛都会给人温暖。大姐夫是砖瓦厂子弟小学的老师,他每天上班坐班车,一走就是一天,到了晚上才回来。大姐身体不好,一直不生孩子,长期休病假,我妈妈工伤在家,她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大姐缝纫活好,能做能裁,我兄妹多,家中无缝纫机,缝缝补补的碎活,大姐就能帮妈妈许多忙。P2-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