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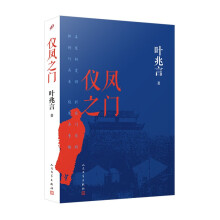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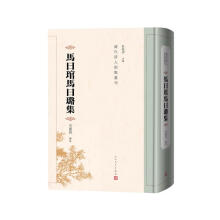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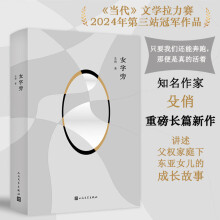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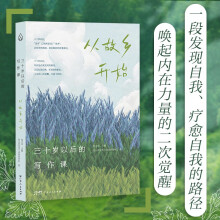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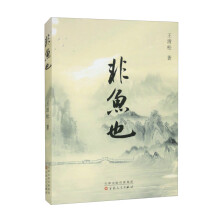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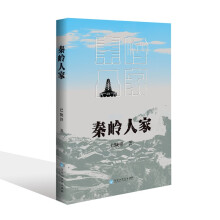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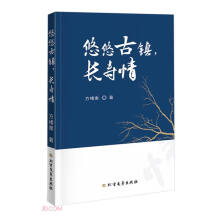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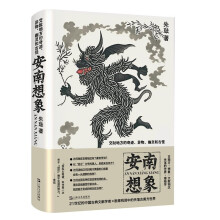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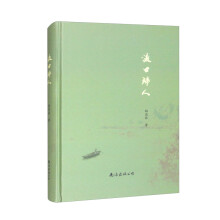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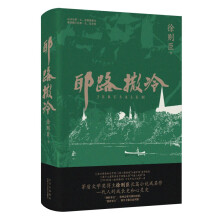
《想往火里跳》是一部女性视角的创业小说,又是一部城市理想者之歌。一群看似谋求财路的中青年,在安放欲望,置放生活的想象的过程中,发现最终追寻的依旧是一个类似古典主义者的情感寄托。在被互联网经济全覆盖的背景下,他们与汹涌而至的时代信息四目相对,渴望用蓬勃的精力,打开不同领域的局限,搭建不同平台的衔接点。然而,这看似朴素的愿望,在实际行动起来,却如同一个去拯救银河系梦想的小小英雄,在半途中,化为一颗小星星。
本书是一部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女性创业史,将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女性成长融为一体,形成复调式的特殊表达。本书是一部深深“源于生活”的小说,整部小说讲述的就是“创业者”与“投资人”之间的反复博弈以求让“公司”活下去的故事。相比于“创业者”⼈物形象前后相对缺乏成长和变化,小说中的“投资人”形象可谓是塑造得相当丰满且精彩。富于力量感,在语感滔滔之势的背面又有所沉默,与创业的重重困境和波翻浪涌的心海同在的,是克制在涛声之外的旋流。
对我来说,2018这一年所过的似乎是我人生中的第二种生活。这第二种生活出现在我面前时,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日子是平板地流畅地过下去的,而且变化的内容也并不特别:每个月去几次北京,在堵车与雾霾的背景前,我和一些影视公司的人,负责投资的人站到了一起。飞机、火车、高跟鞋、西装,容易产生一种职场化的情调。清晨的第一班飞机与夜晚的最后一班飞机也有一种间接的诗意。
所以我日常的一天是怎样的呢?
某个茶馆或咖啡馆。一个或几个男人或女人。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而我是那个约好来谈事的。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那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轻轻飘浮在面前饮料的热气上面——我会跟他们讲我代理的故事,他们会出钱买我代理的故事。
我经常会讲起一个发生在大学男生宿舍的故事。我的叙事是很朴素明白的。主人公发现他的学霸同学因为一次失恋沉迷进了游戏。他想帮助他摆脱出来。他想证明那个女孩并不值得。他是无意中发现一些古怪之处的,女孩因为接到国外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提出分手,但她却在出发的机场不知所踪,而未抵达彼岸。同学的父母也已双双失踪多年。他打开同学的电脑,在GTA游戏里,一个漂亮的NPC用一种凄凉的眼神看着他。然后,开始疯狂地跑,违反程序设定地跑。他操控角色开车追上了她,她无路可走却仍在疯狂地跑。他慢慢看出她跑的路线。SOS。她想要逃跑,想从游戏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他想给她找出一扇门,但是他的背后,传来了他的学霸同学微笑的声音:还是被发现了呀。
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被邪恶男友囚禁在游戏世界的故事很有吸引力。一个发生在美丽校园的危险故事。(一年过去了,我还是没能把它卖出去。)过去我曾经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已婚的催眠大师想摆脱纠缠自己的婚外情人,为她做了一次催眠,唤醒的口令就是:醒不来。“她在稠雾中寻找一扇能让她离开的门。她打开一道又一道门,发现自己总在一道门后。在那些门的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稠雾已经消逝,她将在这片空无里,过完她的一生。”
我极力推荐这个故事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恐惧。这一次,我对面的两个男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恐惧而沉默了。第三个男人早已提前离开。沉默笼罩着我们。我有一点恍惚,我可以源源不断讲述故事,而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想遇到山鲁亚尔,他会购买我代理的一千零一个故事,把我从资金匮乏中解救出来。为什么我愿意离开我写作者的书桌,出来兜售故事呢。我已经写了很多,有些完成得相当困难。从上学的日子起,我就一直在写。为了成为一个作家,我有过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三十岁后我才发现,作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出过多少书,有过怎样的名声,都没法帮助一个写作者固定在作家的位置上,一直待在那里。那种特殊的焦虑就是我这个西西弗斯的石头,自重太大,总是把我从山顶一路带到山脚。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石头上附着所有我已经完成的东西,一起嘲弄着我。必须再一次去开始另一次写作,再一次开始上山下山那折磨人的过程。
我出来兜售故事之前,写作的意志已经崩溃。有几年时间,我一直想写几个知识分子。构思已经成熟,却因为史料庞杂极为劳人,比如我想用鬼故事的写法写写胡风,鬼魂自然是方孝孺的,他一再讲述自己的故事,想阻止胡风写下三十万言书。一开始,我被自己的构思弄得十分兴奋,我想像个历史学家那样,从各种因言获罪的事件中抽象出某种原则。我的努力是白费的,虽然有整整一年时间我生活在我找来的那些文献之中。鬼魂们袖手旁观,不愿帮我重构自己的命运。
目 录
一个嚼着玻璃凝视深渊的人物形象 / 001
想往火里跳 / 011
置身事外与涉身其中 / 183
水下与钢索 / 197
写小说失败,去创业有前景吗? / 206
秘密坐在其中 / 230
温馨提示:请使用湖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走走中篇小说《想往火里跳》:创业之外的线索与心境
在我试图想要谈论走走的这部与她现实生活血肉相关的新作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言说上的困境,即我该如何评论?我们可以评论一部文学作品,但我们如何能够评论一段人生?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既然这是一部深深源于生活的小说,我不妨也借用一点小说中(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工具来帮助解读这篇小说。即借助小说中“走走”带领她的技术团队所开发(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走走所开发)的文本分析软件“一叶故事荟”来分析这篇小说。在分析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投资人”“公司”“创业者”等一类词汇皆是小说高频词。相信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对于这个数据分析结果丝毫不感到意外,毕竟简单概括起来,整部小说讲述的就是创业者与投资人之间的反复博弈以求让公司活下去的故事。相比于创业者人物形象前后相对缺乏成长和变化,小说中的投资人形象可谓是塑造得相当丰满且精彩。小说中出现了多位投资人,作者在小说中大胆地抹去了所有投资人的名字,只凭借其人物刻画技巧完成对每一个投资人形象的勾勒。这种近乎速写式的笔法反而凸显出了每一位投资人在听“走走”做宣讲时的姿态与神情,以及其当下内心的判断和想法,乃至背后更深层次的人物性格,进而聚合成了某种当今社会中的投资人群像。
而令我感到意外的一个数据观察结果在于,“母亲”在这篇小说中的词频竟然比“投资人”还要高。小说的确花了不少篇幅来讲述主人公童年的故事与其创业后和家人相处的生活,但我们似乎总是更容易将目光聚焦于小说主人公创业有关的内容,忽略了其成长的经历以及家庭生活的一面。
我们可以将小说的故事主线概括为主人公创业过程中接连遭遇失败的故事,但小说情绪最消沉的点却在于主人公的亲生父母当年因投机倒把而入狱,自己被人领养这个一笔带过的简约细节,实在是很令人玩味。“做生意”成了“走走”生命中的某种原罪或禁忌,所以养母才会在发现少年“走走”通过租售沙包、鸡毛毽子、铁环挣钱或者倒卖冰棍儿赚点小钱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愤怒。这种原罪一直延续到小说最核心的创业故事之中,甚至于最终成为了小说主人公的某种宿命:“我亲生父母的命运会影响我一生,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都怀揣着他们注定失败的命运。它无处不在。”就此再来重新审视父母当年入狱这个细节,其完全可以看成是全篇创业失败故事的原型,更是后来一系列悲剧情调的起点。而小说在进行到三分之二处时(创业已经遭遇到连续地失败打击)才提起这个细节,其追溯和隐喻的意味就更加不言而喻。
此外,另一个让我颇感兴趣的观察结果在于,在整篇小说的“场景高频词”统计中,“脸上”竟然居第一位,甚至高于一般严肃文学中最常见的场景词“心里”。小说把“心里”所想一类的句式转化为更多复杂的表达可能。作为一篇用了相当篇幅书写创业者接连面对各种投资人的小说,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无数次的“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因而我们就会接二连三地看到诸如“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他黝黑的脸上挂着的谦虚纯朴的笑容”“然后他脸上的笑容开始松弛下来”“皱纹密布的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之类的句子。初次见面意味着不可能有深入对方内心的了解,而投资人与创业者见面开会的故事场景又决定了动作描写的必然匮乏,因而投资人与创业者的表情就成为了他们彼此间沟通与揣测对方态度的关键。而对于彼此间表情的展现最终落实到场景词上面,就是“脸上”一词的反复出现。
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走走的这篇小说与现实生活是如此难解难分,甚至于在小说进程过半的时候,主人公“走走”也开始打算写一本记录她创业历程的小说:“大概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要写这个小说。”她还曾为小说的叙事人称选择与人物最终结局与朋友们发生争论:“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你曾经设想过,在它用第二人称说话的第二声部,你要让你的主人公去死。她可以从开煤气、吞服安眠药、割腕、上吊、跳楼这几种自杀方式中选择一种。你的朋友们(他们也是你的第一批读者)极力反对。”而后来,她也真的开始了关于这部小说写作的准备工作:“你重新布置了书房,把写字桌搬到了窗边。你只需要新建一个空白文档,并为它命名。”至此,现实中作者创业的故事和这篇小说的创作之间在文本内外都得到了完美的衔接。最后让我们重新来看小说的题目:《想往火里跳》,既指主人公创业后有一种“跳入火坑”的煎熬感,也表达出她飞蛾扑火般的决心,同时还留下了一层浴火重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