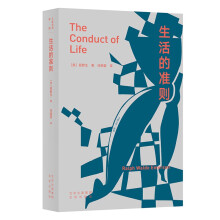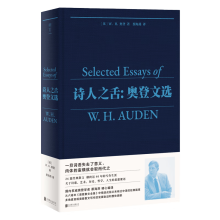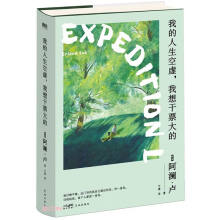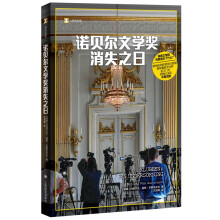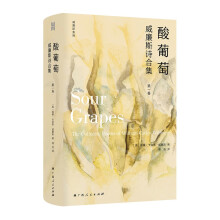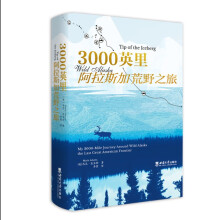a、特罗洛普是英国文学史上**产最伟大的小说家,他作品的阅读量在英国排名第一,是与莎士比亚、狄更斯齐名的作家。b、他拥有许多追随者,从勃郎宁、托尔斯泰,到伍尔夫、亨利·詹姆斯,各方对他的赞许如出一辙,就好像各位作家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注意到了一个风格化的问题。“他的伟大之处,他无法估量的价值,”(语出亨利·詹姆斯)“在于他对平凡事务的纯粹的欣赏。”c、他最有名也最能代表他的写作才能的,是六部一组的两组系列小说——“巴塞特郡纪事”和“议会小说”,《巴塞特的最后纪事》是巴塞特郡纪事系列中的最后一部,一直有文学以及英剧爱好者呼吁“译文社重版特罗洛普《巴塞特郡纪事》六部一组的系列小说!缘其多年未再版,精装本孔网**价已达6000元,平装本200元,以致读者难觅其踪。若能再版,定是外国文学爱好者之福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