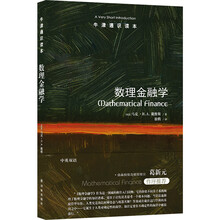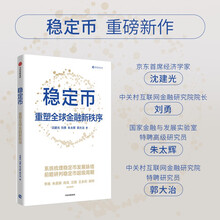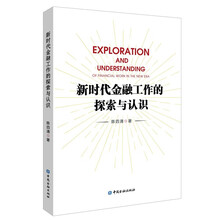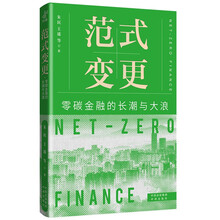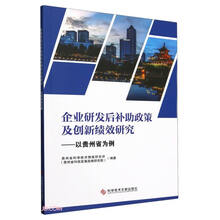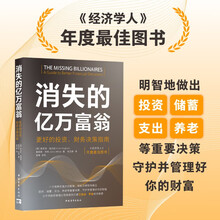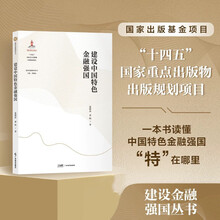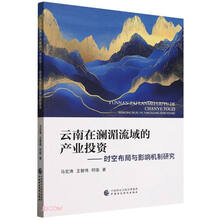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福祉也由“先富先好”转向“包容平等”。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99.09万亿元,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元增长至2019年的70892元(国家统计局,2020)。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全面确定,同时,我国在金融发展、贫困减缓及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障碍。
1. “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金融体系构建与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都有着显著的提高。以经典的M2/GDP表示的发展规模上看,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由1978年的0.32上升到2019年的2.03,远远超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2019年金融深化发展程度(居民储蓄/准货币)(Hao,2006)达到56.2%。
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促进了金融部门的多样化发展,除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外,大量金融中介不断涌现,如区域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及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中介也陆续成立,虽然其存款和贷款来源都有相应的限制,但是从事有选择的银行服务和非银行服务业务不断扩大(Allen et al.,2005)。1994 年后,我国又陆续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三个政策性银行,城镇信贷公司转为商业银行,允许非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成立,减少政府对贷款分配的干预,以及放松对利率的管制等。在全球经济金融化趋势日渐增强的情况下,我国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邮政储汇局、其他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外资金融机构等)发展迅速,总金融资产总量由 1978 年的 0.33 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54.41万亿元 。现在,我国多样化的金融体系已经逐步完善,主要由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构成,大大增加了金融服务获得的可能性,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可获性大幅度提高。
2. 贫困减缓成果显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我国一直致力于贫困减缓工作,并取得突出的成就(表1.1)。
表1.1 我国贫困人口与贫困率
a)1978~1999年称为农村贫困标准,2000~2007年称为农村绝对贫困标准;b)2000~2007年称为农村低收入标准,2008~2010称为农村贫困标准;c)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2 300元/人/年(2010年不变价)
资料来源:1978~2017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2018年和2019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20)
作为世界上*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曾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我国的贫困标准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进行调整,根据2010年统计标准,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 039万人下降至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9年的0.6% ,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剩余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恩格尔系数 是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该比重越大,意味着一国或地区越贫穷,从这一角度看,恩格尔系数可以测度贫困,并成为底线公平的一个指标。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均明显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9年的27.6%,下降了29.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5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19年的30%,下降了37.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55.7%。1978~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如图1.1所示。
图1.1 1978~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减贫的效果得益于我国在不同时期的减贫措施的实施:改革式减贫(1978~ 1985年)、开发式扶贫(1986~1993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综合扶贫(2001~2010年),以及转型式扶贫(2011年至今)。在众多的减贫措施中,金融发展减贫的作用逐步发挥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信贷扶贫到微型金融、保险等多种方式的出现,以及当前的普惠金融发展等,金融在贫困减缓这一底线公平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至2019年的42 358.8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也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至2019年的16 020.7元,1978~2019年我国人均GDP与居民生活水平变化如图1.2所示。
然而,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不平等程度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收入差距的警戒线为0.4 ,而从我国各年基尼系数看(图1.3),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已经超越了这一警戒线,并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流向富裕人群和低收入人群(较低收入的50%人群)的比重由27%∶27%,改变为41%∶15% ,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已接近一些不平等状况严重恶化的非洲及拉美国家”(陈志刚和王皖君,2009)。我国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地区居民、高低收入群体等收入差距较大,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也为社会稳定运行带来不利的影响。
图1.2 1978~2019年我国人均GDP与居民生活水平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图1.3 我国基尼系数变化
资料来源:2004年及之前数据来自程永宏(2007)(1991年数据缺失);2005年之后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从理论上看,包容性金融发展是金融发展研究的重要构成,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缺乏关于“制度—包容性金融发展—社会公平”的机制分析,同时缺少以我国为样本的检验。由此,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第一,在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金融发展理论和社会公平理论基础上,构建“制度—包容性金融发展—社会公平”的综合分析框架,丰富了理论研究成果,追踪了学术研究前沿。
第二,在制度视角下探讨包容性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识别其作用途径,为提高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展了研究范式。
第三,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用双重差分和系统广义矩的方法进行经验检验,并比较分析结果,补充了实证和应用成果,丰富了相关的文献。
(2)实践意义。本书探讨包容性金融发展的社会公平效应及制度在其中的作用,提出促进我国包容性金融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与对策,对于完善我国“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金融体系构建与深化金融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我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借鉴思路,进而为实现改革成果公平共享与“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综上,本书以包容性金融发展为研究对象,从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研究领域的前沿出发,系统分析包容性金融发展的社会公平效应及地区制度质量在其中的作用,能够为我国深化金融改革、包容性金融发展战略实施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为推动改革成果共享与社会公平实现提供借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