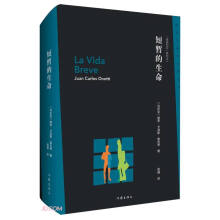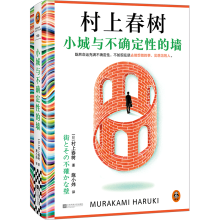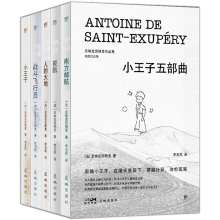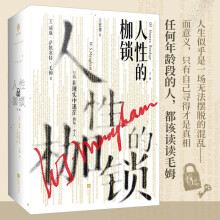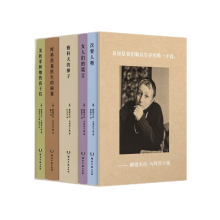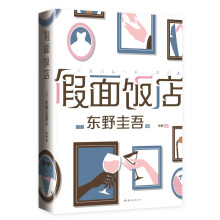窄 门
我在这里叙述的故事,别人可以做成一部书,在我则是全身心投入的生活经历,我的道德观念也受到重大挫折。因而我只是把我的回忆草草写下,有的段落支离破碎,也不求助于任何虚构去补缀拼凑;我说出这些往事,原不指望有多少乐趣,任何矫揉造作的努力更会把仅剩的乐趣一扫而光。
我丧父时还不到十二岁。母亲在父亲行医的勒阿弗尔市里再也没有什么眷恋,决定搬到巴黎去住,她认为我在那里可以更好地完成学业。她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阿斯布尔顿小姐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小姐没有家,起初是母亲的教师,后来是她的伴侣,不久成了她的朋友。这两个妇女都是面容温和凄恻,我随同她们一起生活,她们在我的回忆中总是像穿着丧服似的。有一天,我想,已离父亲过世很长一段时间了,母亲用了一条玫瑰红缎带换下晨帽上的那条黑缎带。
“哦! 妈妈!”我惊呼,“你用这个颜色难看极了!”
第二天,她又缀上了一条黑缎带。
我的体质向来孱弱。妈妈和阿斯布尔顿小姐时时刻刻操心的,就是防止我累着了,这份操心没有使我变成懒汉,这是因为我实在喜欢学习。刚入初夏,她们俩人一致认为是我到乡下去的时候了,我在城里脸无血色;将近六月中旬,我们前往勒阿弗尔附近的封格斯马尔,每年夏天布科兰舅舅在那里接待我们。
布科兰一家住的是一幢白色三层楼房子,跟上两个世纪的许多乡村房屋很相像;四周一座花园,不是很大,也不是很漂亮,与诺曼底的其他许多花园也没有明显的差别。房子朝东对着花园前面,开了二十来扇大窗子。后墙也有那么多扇窗子,两侧没
有。窗上都是小玻璃格,有的是不久前新换的,在发黑发绿的老玻璃格子中间显得很刺眼。有几块玻璃上有瑕疵,被亲戚们叫作“砂眼”;通过砂眼看出来的树弯弯扭扭;邮差经过砂眼前面会突然变成驼背。
长方形的花园四周有围墙,在房屋前面形成一块绿荫覆盖的大草坪,绕着草坪是一条沙砾路。这边的墙头砌得矮了下去,可以看到包围花园的农庄院子,按照当地的做法,一条山毛榉道路作为院子的边界。
房屋背面朝西,花园布局更为舒展,南面贴墙的果树前是一条鲜花盛开的小径,有一排葡萄牙月桂树和其他树做的厚屏障,挡住了海风。沿北面的墙边另有一条小径,伸入树枝下面不见了。我的表姐妹称它为“暗道”,一过黄昏都不愿意冒险再往里面钻。这两条小径都通往菜园,菜园是花园的延伸,不处在同一平面上,要走下几级台阶。然后,菜园尽头的墙上开有一扇小暗门,墙外是矮树林,山毛榉道路的左右两侧都可以到达那里。从西面的台阶,目光越过连接高原的灌木,欣赏到满山遍野的庄稼。离此不远的地平线上,一座小村庄的教堂,黄昏风静时,有的房屋冒出袅袅炊烟。
夏季,每个晴天的晚上,我们在饭后到“下花园”去。从小暗门出去,坐到路边的一条长椅子上,在这里乡野景色几乎一览无遗;舅父、母亲和阿斯布尔顿小姐坐在一座废弃的泥灰岩矿的茅草棚顶旁边;眼前的小山谷里雾气弥漫,远处的树林上空夕阳余晖。然后我们又到已经昏暗的花园角落里停留一会儿。我们回去,在客厅里见到舅妈,她几乎从不跟我们出去……对我们孩子来说,晚间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还经常看书,过后会听到做父母的上楼的声音。
我们白天的时间不是在花园里过,就是在“学习室”里过,那是舅舅的办公室,里面放了几张课桌。表弟罗贝尔和我并排坐着做功课;在我们后面是朱丽叶和阿丽莎。阿丽莎比我大两岁,朱丽叶比我小一岁;罗贝尔在我们四人中年龄最小。
我在这里叙述的不是我的最早的回忆,但是只有这些回忆与这个故事有关。我要说正是父亲去世的那年这个故事开始了。可能是丧事,也可能即使不是自己悲伤,至少是见到母亲悲伤,使我的情绪过分激动,也唤起我心中其他新感情:我过早地成熟了;那年我们又来到封格斯马尔时,朱丽叶和罗贝尔在我看来还稚气未脱;但是看到阿丽莎时,我突然明白我们两个人都已不是孩子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