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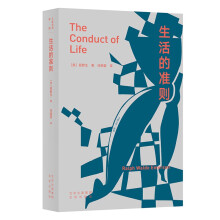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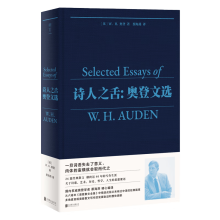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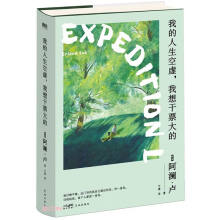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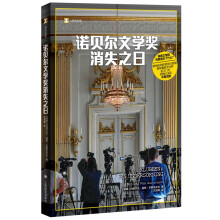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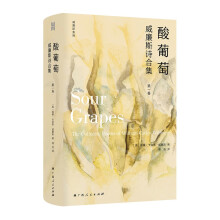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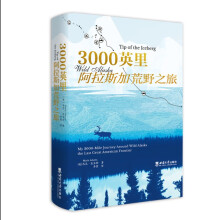
第一章 周日的意外
视窗电视台节目负责人阿图尔·拉多瓦尼给我打来电话的时间是周日,下午四点钟。周日,午后,我通常眯上一会儿,把手机调为“静音”,拔掉家里的座机线,放下窗帘,关掉电视,再盖上一条柔软的毛毯,躺在沙发上小憩。大约一个小时而已。
那个周日,正下着绵绵细雨,雨水轻轻敲打着窗子,短暂地打个瞌睡在我看来显得无比甜美。进入梦乡前,我一贯想些愉快的事,或者至少,有趣点的事。那天,我在法国《世界报》的网页上才看了旧时代一位中国演员的口述。这个人现在住在纽约,已经到了显老的年纪,他说险些没逃过一场可怕的惩罚。恐怕一拨演员之中,他是唯一侥幸逃脱的人。因为,在那个时期,剧院里上演的戏,光是手就能当主角。妙。到这里一切都很正常,符合当时的逻辑。但是,接下来,这位中国演员说,所有扮演过这个角色的演员,一个个都死了。要么倒在家门前,要么死在浴缸里,要么淹死在湖里,或者干脆中毒,死在床上。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谁杀了这些演员,原因或者动机又是什么。没有任何证据……什么都没有。
我正遐想着是谁、为什么、在什么地方如此作为,联想到那里的街巷,那里的一切。那平白无故的心绪不宁、胡思乱想仅仅也就过了十分钟,座机就疯狂地响了起来。显然,我忘了拔掉电话线。
闭着眼,我想到——此时此刻绵绵的雨停了,死去的魂魄在黑暗中也黯淡了下去——这位周日下午四点叨扰的不讲礼貌的人,在电话响过五六声后会撤退的。但是,没有。刺耳的电话铃聒噪了十五声方才停下来。我心想,他放弃了,于是把毛毯罩在头上。令人昏昏欲睡的絮语声又回来了。或许,在我的梦里,一个湿漉漉的街角上会出现某个令人恐惧的军人。我再也睡不着了,我想,但是,至少我得略微平复一下电话铃声对我脑子造成的冲击。
说起来,那天下午我有罪受了。戳破我脑壳的电话铃声执拗地聒噪了整整七回,每回都得响上十五声。第八回,我飞身跃起,冲到我的灰色座机兀自杵着的床头柜前,愤怒至极地操起听筒。
“您好啊!”
电话线另一端的人最好还是把话筒放下,否则就会再次听到我发出的貌似问候的沙哑咆哮。
“您是杜卡女士吗?”男人用喉音说。
“不,我不是杜卡女士。”我回答。
另一头儿是犹豫的沉默。
“对不起,”低沉的嗓音说,“有人给了我这个电话号码,找杜卡女士。”
“这里没有杜卡女士,”我接着说,“您打错了。”
“是吗?对不起。”声音有些含糊地说,接着挂了电话。
我又回到了沙发上。杜卡女士!
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打开意利咖啡机。你等我把咖啡煮好,我对自己说,再倒到杯子里。
我才把咖啡倒在杯子里。
电话铃声又响了。响了四声。
“您好!”
“您是杜卡小姐吗?”还是那个低沉的嗓音,竭力显得通情达理。
“是啊?”
“我是在和杜卡小姐说话吗?”
“是啊?”
“您是莉莉安娜·杜卡吗?”
“是啊?”
“我是阿图尔·拉多瓦尼,杜卡小姐。”
“是啊?”
电话线那头的人彻底晕了。他原以为著名的阿图尔·拉多瓦尼给我打电话,我得高兴死了。在周日下午四点钟!这个人不是在做节目吗?在他任职的电视台,周日下午的节目里,他常常喋喋不休。
“请原谅,”他继续说,还是完全如坠云雾之中,“但是我去过您的办公室,他们引我来找您,我一点也不想打扰您……您理解我吗?”
“不理解。”
“莉莉安娜小姐……您的上司让我来找您……”
我醒了。他一共说了四回以“指向”在阿尔巴尼亚文中,drejtohem、drejtoj与drejtues的词根都是“drejtoj”(指向),故有此说。为词根的词。他们引我,我找您来,上司……他言辞太贫乏了。
“我明白了,”我决定放过他,最后说,“请讲。”
“我想要马上见到您,我有一件急事。”
这个人竟然如此不明事理,挂电话的时候我想。他在哪里学的说话,电视台那儿吗?
阿图尔·拉多瓦尼希望我们晚上七点在罗格纳酒店的酒吧见面。当然,我不再躺在沙发上了,而是给我的美发师打了电话,问她六点是否有空,给我简单梳个头。然后,我走到卧室里,打开了衣橱。我的衣橱很大,是从一个手艺很好的木匠那里定做的,占了四面墙。在一面墙上有些简单的服装,牛仔裤、T恤衫和运动外套。另一部分挂着时尚西装、丝绸衬衫,下方的抽屉里摆了我很少穿的高跟鞋。窗户两侧的墙上分别是大衣、风衣、棉服、毛衣等等;都是依照我着装的意图摆放的。
第一次与阿图尔·拉多瓦尼见面,不论他的意图是什么,我都会穿黑色西装去,但配的是短裙,而非西裤,还有乳白色丝绸衬衫。再搭上带跟的黑皮鞋。
从他的语气,我已经感觉到,上司把他“推给”我令他不悦。我必须在外表和气势上压过他,让他态度温和些,不要一开始就张牙舞爪。
我把西服放在床上,走到窗前。雨还在下,现在下得更厉害,并非摇篮曲似的雨了。我应该坐车去,否则必得挨淋,头发一定会乱的。
阿图尔·拉多瓦尼,这个名字对我没有多大意思。我知道他在视窗电视台负责综艺节目《魔眼》——一档类似于《老大哥》全球流行的游戏真人秀,1999年在荷兰首播,后在各国播出了不同版本。节目要求参与者生活在一所一举一动都被摄像机和麦克风记录的房子里,不允许他们与外界接触。的真人秀。近两年来,他的节目成功超越了后者,夺走了一大批观众和赞助。他还常常参加电视上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谈话节目,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个稳重而专业的人。
我慢慢地穿好衣服,一边思索着究竟为何阿图尔·拉多瓦尼到我们事务所登门拜访,身为上司和老板的我舅舅又为何选了我来摆平他的事。
我们事务所,或许是目前阿尔巴尼亚唯一的调查机构。事务所的门牌上写着“私人纠纷处理机构”,路过的人瞄上一两眼,都搞不太明白我们在解决什么样的私人纠纷。实际上,我们就是实打实的侦探,与电影和书本里的那些人没有任何不同。我们总共三个人,全都忙得要死,而我舅舅埃米尔·阿巴兹却不想增加人手。他的理由是,选人不是件易事,做侦探必须得有兴趣、有本事,目光敏锐、头脑聪明,既有文化知识,又了解情况,具备极其迅速收集信息的渠道,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有多难找。
我舅舅说,他以前曾就职于安全机关,在抓窃贼的部门工作,但是没什么人相信他。看他工作时的样子,我也不相信他只是抓一般的窃贼,但是说到底,谁又还在乎他的过去呢。开事务所的时候,他找来了他的前同事穆罕默德·哈吉伊梅尔当合伙人。他又把我找了来,理由是我打小时候就热衷于剖析形形色色的隐秘,这热情人尽皆知。
实际上,我一直失业。二○○○年,我读完法律系,该找的地儿都找了,但就是找不到工作。有一个女律师协会让我干了五个月志愿者,帮助受虐待的妇女,捍卫她们的法律权益,但是由于女律师们根本筹集不到经费生存下去,我就离开了。在一家橙汁生产企业、一家建筑公司里,我又混了大概两年;还是由于缺乏资金,他们也停发了我的工资。
那段时间,我一如既往地啃着探秘和谋杀的书。我就这样把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一切当成了消遣:我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约翰·格里森姆、约翰·勒卡雷,还有当代的一些人,想象自己成了现代版的夏洛克·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让我相当疯狂,虽然我并不像她年纪那么大。实质上,那是一段痛苦的时期,因为我无法谋生,仰仗着父母度日,在我看来,这太无法让人接受了。
此间,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舅舅埃米尔,他认为自己在布洛克区地拉那市中心的一个区域,东欧剧变前为高干住宅区。的一幢大厦里干保安已经干够年头了,足以让人们忘记他前特工的身份,便决定出去闯一闯。当时,他已经替几位重要人物解决过麻烦,他们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在这些成功的尝试并蛰伏了十年后,他自己下定了决心,是时候干点事了。
一月的一个夜晚,隆冬时节,是没有人到外面去、都往暖烘烘的房间里一待、看电视上放恐怖片的日子,阿斯德里特舅舅即埃米尔·阿巴兹。突然造访我们家。他打断了我们正在欣赏的惊悚情节,把我们推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隐秘气氛之中,让我们在那约莫两个小时里吓得发抖。
……
温馨提示:请使用湖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