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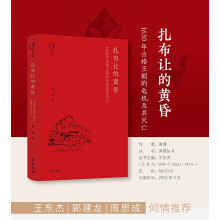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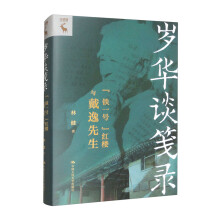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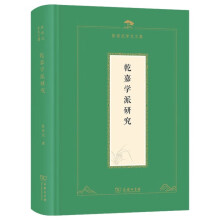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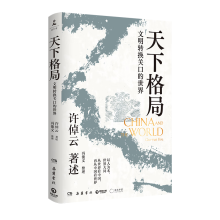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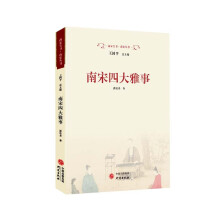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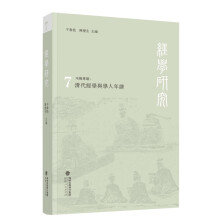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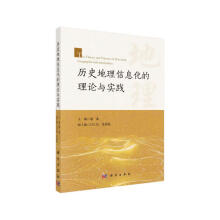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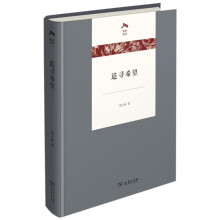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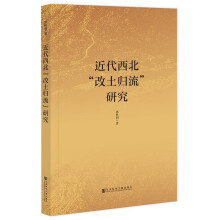
明成化汉水改道之初,汉口并非宜居之地;因地势低洼,常年泥泞潮湿,湖塘、河滩生长着大量芦苇,遂为芦荡泽国,民众难于栖身,直至天顺年间始有定居者;不过在没有定居者之前,亦不乏附近的汉阳县民人前来垦种和渔猎。为什么说天顺年间才有定居民众呢?因为,据嘉靖《汉口地课碑记》可知,明中期汉水改道前夕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5)已有民众在汉口建房居住,但直到明嘉靖初年,汉口不过是一个渔村,渔民们在此垦种和渔猎,须每年向汉阳县三沦河泊所缴纳渔课。渔业是明代汉阳民众的重要生计来源之一,也是当时地方政府重要税源之一。明成化之前汉水河道并不宽阔,汉阳民众只需划着一叶小舟就可以过河来到汉口地势低洼处的水塘、湖泊等水域进行渔猎。实际上,汉口不仅吸引了汉阳民众前来获取生活物资,还招徕了一江之隔的武昌县的民人萧氏一家前来承佃租种,成为明代汉口基地的早期开发者。这亦可以看做是汉口由芦苇荒滩发展为小渔村的历史写照。
然而,汉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自成化汉水改道形成新的稳定入江水道起,也为孕育和发展除农垦、渔猎之外的商业经济活动埋下伏笔。汉口作为天然良港,自然离不开船运贸易。随着明天顺年间不断有居民来此筑屋定居,商船靠水口两岸停泊,汉口市场渐开。同时,因为早期商业活动以船运和水口两岸商品集散为主,汉口遂有船码头之称。是故,从渔村到船码头可以看做是汉口早期开拓的缩影。相比之下,明嘉靖之后汉口的成长速度与规模则堪称晚明时期全国新兴市镇之翘楚。隆庆六年(1572),汉口商业税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所缴纳的数额相比增加了3倍多,仅仅三十年光景,汉口在商业上就超越了当时同样归汉阳县管辖的著名码头市镇刘家隔;当然刘家隔的衰落与竹筒河淤塞、汉水改道造成的致命打击不无关系,而得江、汉之便的汉口吸引更多的拓荒者和商民来开发并快速崛起,更加加剧了后者的衰微;可以说,自明嘉靖以后,汉口凭借自身的贸易区位优势取代了此前刘家隔市镇的商业中心地位。正是在嘉靖朝,汉口已发展为以“仁义礼智信”命名之五坊组成的商业市镇。嘉靖《万历府志》卷二《方域志》曰:“居仁坊、由义坊、循礼坊、大智坊、崇信坊,俱汉口地方。”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坊厢始末》认为,坊厢制起源于明洪武年间,编户置于城内者为“坊”,置于城外(廓外)者为“厢”;“有人丁而无田赋,止供勾摄而无征派”。 汉口作为邻近汉阳城区的市镇,靠农业谋生者极少,市民大多“惟贸易为生”,自然是编入“坊”管理为宜。不过,商民起初主要集中在水口南岸一带,因此“汉口巡检司在县治北三里、汉水南岸”。质言之,五坊的创置和巡检司的设立,是明代汉口由船码头向市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商人自行选择汉口作为新的转运口岸,以及万历朝汉口成为湖广漕粮外运和淮盐、粤盐集散总码头,必然会促进汉口市镇规模的拓展。举凡粮食和食盐这样的大宗货物的转运和分销,必定需要大量脚夫、水手、船夫等苦力为之服务,并吸引各层级分销商人乃至贩卖私盐者纷至沓来。该时期汉口的人口急剧增长当与此有莫大关系。譬如,当汉口市镇的人口数量达到如前引万历朝(1573—1620)郭文毅《正域重修免溺堤记》所称的“汉口几万家”规模时,与嘉靖二十一年(1542)整个汉阳县才三千余户的规模(即使按每户五口计,此时汉阳县占籍总人口尚不足2万人,加上汉阳县并非商业著称的大县,即使有未占籍人口,亦应有限)相比,相距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汉口作为新兴市镇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可谓不壮观。若加上大量的流动人口和难以计数的长短期雇佣劳动力,实际在汉口谋生的人口数量当更庞大。其拓展速度和规模在古代中国市镇发展史上亦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与武昌和汉阳相比,汉口在吸纳移民和扩展商业贸易方面的能量更加突出。其商业辐射能力和财富积聚体量不仅超过武昌的老牌市集金沙洲,而且将臻于鼎盛的汉川刘家隔市镇远远地甩在后面,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口在16世纪的发展规模已超过隔江对望的省城武昌,成为湖北最大的城市。不仅如此,明末汉口镇的商业声望已盖过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成为“天下四聚之首”。
温馨提示:请使用湖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