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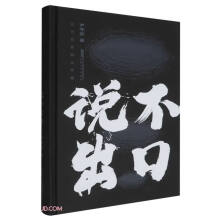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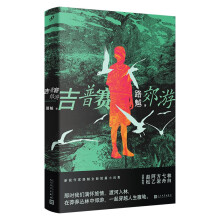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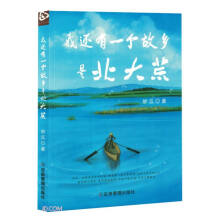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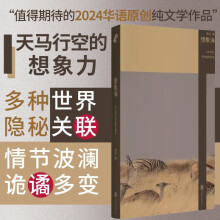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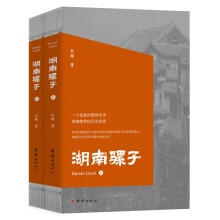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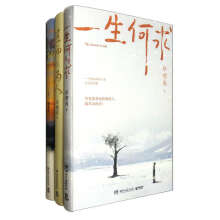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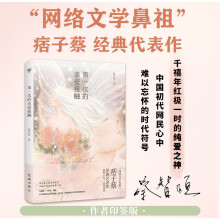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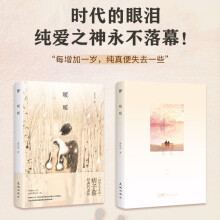
一个人被交换的半生
童年被过继给大伯家,在大伯母如愿生子之后回到原来的家,一个哥哥,成为弟弟,在两个家庭中都无法找回位置,彻彻底底成了局外人。兄弟俩互相艳羡着走完了童年,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抉择之后,成为了两个破碎的中年人。互换的大半生,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时代转型,命运却无可转圜
小说主人公梁为民,上过卫校,当过乡镇医生,经历过医疗事故,到北京的医院打过工,因为内心坚守毅然出走,开始在中关村电子创业大潮中翻滚。那是一个火热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普通人的际遇总是带着十足的偶然性,一路向前,半生、一生,也这样过下去。
他的全部努力,也没能完成普通生活
小人物的命运被偶然的浪潮拍打,最终沉淀下来,在忙碌了大半辈子之后,他们得以在人生路上稍作休息,回忆起童年至今种种,梳理兄弟俩的前半生。原来,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人间事,悲欣交集。
本质上,写小说也是劳作,既然是劳作,也就和种庄稼没有太大分别,字斟句酌如拣选种子,谋篇布局类安排五谷杂粮。所以今天不妨把对小说的一种理解简化为—写小说如种庄稼。
如今,不要说年轻人,即便是中年以上的人们,大概都不怎么看见真正的庄稼了。我们眼里只有磨好榨出的米面油,甚至只有餐厅里烹饪好的食物、面包店烤好的面包,无人知晓这些事物最初不过是一粒种子,因为投入了大地,因为有农人悉心侍弄,因为阳光雨露,才长成一株禾苗,才结出或酸或甜的秋实。再然后,才是我们日常所见所用的样子。
我在乡下的完整生活有二十年。其中的八年,从小学到初中,每年都会有几段时间非常亲密地接触庄稼。这些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在为我提供真理。春天,跟着在牛马的屁股后面,把一枚又一枚豆籽点进田垄;也可能是端着簸箕,抛洒土肥去覆盖母亲点下的种子。不论做哪样,大人都只有一个要求:别太稀了,也别太密了。这尺寸他们已了然于胸,而我却难以摸到门路。夏日,放农忙假,跟着大人去薅草。谷子长到一拃多高,在干爽的土地上摇摆。我看见田垄中一丛丛密密的苗,高兴地跟母亲说:“谷子真好啊,你看长得多密。”母亲头也不抬,一边蹲着向前挪动,一边说:“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的不是苗,是没苗的地方。”琢磨了许多年,我才明白大致的意思—一株庄稼长得好坏,能从自身的高矮粗细看出来,可一地庄稼的好坏,看的则是苗和苗之间的距离。距离太近,甚至生到了一处,这些苗就会因互相侵蚀而孱弱细瘦,甚至一粒粮食也结不出来;距离太远,一条垄也没几株苗,照样收不了多少粮食。它们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太稀又不太密—既不近到互相影响,又不可远到无法彼此呼应。
写小说又有什么不同呢?字词字句,既要有章法,更要有文气。文意总在空白处,那些没写的东西,才是要写的东西。所以,字和字的距离,就是苗和苗的距离,必须恰当、合适。恰当与合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看土壤、水源、天气、种子,更要看写作者对这门活计的熟练度与理解力,所以写作总是随时而动、随势而动,也是看天吃饭的活儿。
说到这,忍不住又想起一样庄稼,玉米。我小时候遇见过两块至今仍在记忆中生长的玉米地。
第一块地里,有两家的玉米,我们的和邻居家的。我家的玉米比邻居家的矮一个头。我心里难过,便说:“咱家的玉米怎么长得这么差。”父亲却掰掰正在成形的玉米穗说:“好。”从地东头走到地西头,我终于忍不住问:“明明比别人家的矮那么多,怎么还说好?”父亲说,你不知道,现在的玉米都是改良种,有百天种,有九十天种。我们种的是百天种,一百天才成熟,别看它长得矮,可是一亩地打出来的玉米,可别九十天的多。
另一年,又看到一片玉米,长得一株挨着一株,密不透风,所以都不高,甚至根本没有结出玉米穗。我以少年的姿态跟父亲说:“看看,这家人真是不会种庄稼啊,不知道两株苗之间是要留空。”我以为我懂得了农耕之道,并以此去嘲笑的别人,哪想很快就被父亲“打脸”。父亲说,狗肚子盛不了四两油,别又不懂装懂啦。我不明所以。父亲解释说,这片地里种的根本不是玉米,是青贮。青贮本来就不是为了打粮食,而是收割后晒干,留到冬天用来喂牛羊的。所以,种青贮就是要种得密密实实的,这样长得才多,而且因为密,才长得细细的,牛羊吃起来才不会那么干硬。我羞愧而恍然。
写《水落石出》的时候,我想的多是这类种庄稼的道理。
一 刚刚好
二 后遗症
三 换户口
四 兄弟俩
五 错中错
六 梦里梦
七 办婚礼
八 走夜路
九 三胞胎
十 水帘洞
十一 告别信
十二 过新年
《水落石出》创作谈
温馨提示:请使用湖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