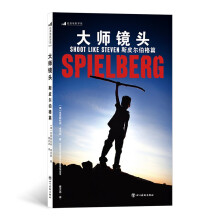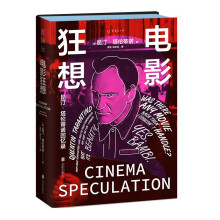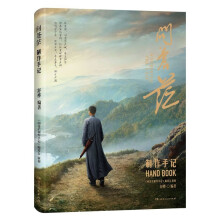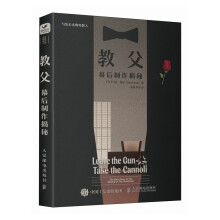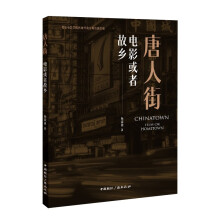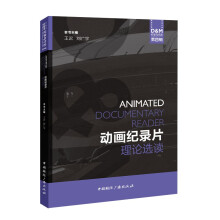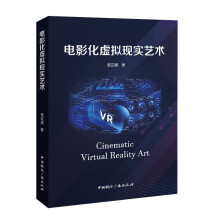如果把一部由我们所创作的戏剧重复演上好多遍,有时我就会失去再次登台的冲动。这天晚上,我还是像往常一样从弗兰卡的化妆间前经过。不用说也知道,在化完妆后,她正温习着自己的台词。只是瞥了一眼,她就立刻猜出了我当时的心情。
“你不用太担心了,”她马上对我说道,“就当是不停说上十分钟的笑话嘛。表演烦躁症马上就会消失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就能每晚都保持相同的情绪呢?还有,那些拗口又难记的台词,你又是怎么从容应付的?”
“这很简单,你也可以轻松做到,只要想象:你的父母都是演员——就像我父母那样。在你小的时候,他们每晚都会把你和服装还有道具一起,带到剧院的后台,然后把你安顿在一个铺有毛毯的大箱子里。当他们开始把道具搬上舞台的时候,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无论是舞台工人还是演员的声音,又或是陆续进场、窸窸窣窣的观众,都不会打扰到你,相反,它们还成了这世上最有效的催眠曲。可是突然,妈妈跑来把你给叫醒了:‘轮到你啦,孩子。记住,我们现在表演的是《悲惨世界》,而你的角色是童年时的柯赛特。还记得第一段台词吗?’‘妈妈,我想再睡一会儿嘛……’妈妈并不理会你,而是把你举出箱子,抱在怀里哄了一会儿,然后用一条湿手帕为你擦了擦脸,接着就把你带到了幕布间。‘去吧,该你上场啦!’这就是每天晚上我所体验的感受。它并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创作并表演了不计其数的喜剧、悲剧、讽刺滑稽剧与叙事歌谣。我开始发现,戏剧也逐渐成为我的生活,每天更甚,直到占据全部。
它不再只是把故事搬上舞台这么简单,不再只是表演笑话或是闹剧。对如今的我而言,每个夜晚都成了独一无二的观众见面会。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表现,又会怎样反应,而你,总会在突然之间,明白了应该如何与他们相处。
在你上台时,第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便是认清:今晚到场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正厅、包厢还有顶层楼座上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如此,你就可以从第一段台词开始,发掘这批观众的情绪、性格与行为方式。不过,可别以为你的分析总是头头是道。有时候,你自以为很有把握的一段台词,极有可能会受到意料之外的冷场:观众并未产生共鸣,有的只是些许零星的笑声。这时你就该想:“可能是我没掌握好抑扬顿挫吧。看看下一个喜剧情节会怎样。”如此,所有的担忧就会像在空中打了个圈一样,呼,一下就不见了。
很幸运,在舞台上,我总有弗兰卡相伴左右。她只需偷偷做出一个手势,就能暗示我减缓节奏,把台词变得更“柔顺”些。我总会采纳她的建议,而且几乎每次的结果都证明,她的决定是正确的。
不过,弗兰卡并不只对我采用手势进行沟通。如果台上或是厅里的某个聚光灯——用行话来说——“跳了”,连灯光师都还没发现,她就已经若无其事地抬起一条手臂来——仿佛只是为了驱赶一只烦人的苍蝇。这个动作会让技术员立刻明白过来,而弗兰卡呢,则会指着舞台上的某个方向,继续重复这个动作。这时,“长条”——弗兰卡为技术员取的绰号——就会缓缓调亮另一盏聚光灯(耳光或是面光),用来代替那盏熄灭的。此外,在音箱放出失真或是过高、过低的声音时,她也会采取相同的办法。总之,什么也逃不过她的观察。要知道,在剧团里,大伙儿都叫她“舞台总管”。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位演员或多或少游离在正常的节奏之外,或者更糟糕,慢了几拍才开始自己的台词。这时,弗兰卡就会立刻重咳几声——当然,总是在不被观众察觉的情况下,并将目光投向那位不合节拍的演员。对方马上就能领会,然后回到正常的节奏。
对我,她会经常采取一个姿势,那就是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这是在提示我:用力收紧上腹进行表演,并发出更低沉也更有张力的声音。事实上,几乎每一位初次登台的演员(而我在开始表演前,根本从未上过专科院校,也没受过专门的发声训练)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轻易抬高头声或是鼻声(更糟糕)。这样的高音不仅难听,而且还毫无用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