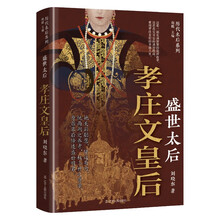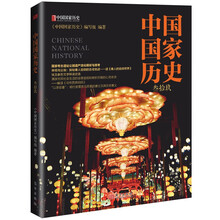《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
周新民:我了解到,你是出生在乡村,有哪些因素推动你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东西:我似乎有点写作天赋。小学时,常写顺口溜或者山歌,被老师选抄到墙报上。读高中时,作文偶尔得到语文老师表扬。看完电影写影评,放进县城电影院的投稿箱,署名“田代琳”的影评被印贴在电影院的橱窗里,还得到电影院奖的4张电影票,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于是,我到图书馆借小说来读,读着读着,就有了做作家的冲动,想把自己遇到的不平写出来。但那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一个念想。
后来考上河池师专中文专业,遇到韦启良和李果河老师,他们本身在写,也竭力鼓励学生们写。看到老师不停地拿稿费,手痒心急,开始悄悄写作,参加学校的“新笛文学社”,听作家老师讲课,参加征文活动。继而,诗歌获奖一次,散文获奖一次,信心爆棚。半夜三更起来写小说,幻想像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喻杉那样一夜成名。稿件一放进邮筒,脑海里就出现画面,想象这篇稿件如何历尽千山万水,到达编辑手里,又如何被编辑赏识,同意发表。十天半月,稿件没发,被退回来了。于是,又改投第二家,还是没发。休息一段时间,找找原因,再写第二篇。那时不敢投太高级的杂志,只投地市级或省级公开发行刊物。内刊发了许多,公开刊物只发表过一首小诗,在《河池日报》副刊上,获8元稿费。领稿费时,柜台里的阿姨问,你的文章发表了?我自豪地点头。她说不简单呀。那年我18岁。
现在回想,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恐怕有如下五个原因:一是过早地了解了人间百态,乡村的生活是叙事的,张家长李家短,我七八岁时就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像今天报纸上的连载小说,每天都有新情节,而且还出人意料。这些生活中的故事,一点也不比书上的故事逊色,黄色的尤甚。二是我有满腔的悲愤和委屈,这和家庭成分不好有关,读书时常被同学欺负,有了文字组装能力后,就想把委屈写出来。三是母亲勤劳、善良,她非常辛苦,却一直供我读书,我无以报答,总想用笔来写写她,写她的辛苦和艰难。四是被作家这个神圣职业所吸引,那时的作家深受读者爱戴,他们可以为民请命,为民代言,还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像鲁迅,以笔为刀。五是欣逢文学最好时代,有老师们的鼓励,有编辑们认真的退稿信,还有远远超出工资的稿费回报。
周新民:你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广西文学》1986年第8期的《龙滩的孩子们》。后来又发表了《孤头山》《醉山》《稀客》《秋天的瓦钵》《回家》《祖先》《地喘气》等小说。我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创作,你都是用本名“田代琳”发表的。从1992年开始,你用笔名“东西”发表作品。我把你用本名发表作品的时段定位为创作起步时期。你曾说“这个时期没有目标,没有定法”。你能回忆一下这个时期你尝试了哪些方法吗?
东西:读大专的时候,常到图书馆翻看最新文学杂志。当时中国文坛被扯得最多的就是“寻根文学”,代表作家是贾平凹、韩少功、阿城、何立伟等。他们所写的乡村与我的家乡相似,一草一木被他们雕刻,乡村的风俗被他们详细描述。越看越有亲切感,特别是平凹先生的《腊月·正月》,仿佛就在写我的村庄,里面人物姓氏与我的村庄人物姓氏巧妙地部分吻合,我就想原来我身边也有文学资源,原来越土的越有价值。当时,作家们写乡土题材就像今天的“80后”写城市题材一样时髦,这大大提振了我写作的信心。虽然,我没有写过类似于“寻根文学”的作品,但我曾经在日记上,笨拙地记录过乡村的生活,甚至记录过一只鸡如何从我面前走过。后来,阅读了先锋小说,莫言的、马原的、余华的、苏童的、格非的、吕新的……由此上溯,阅读了卡夫卡、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加缪、萨特……那时被罗布·格里耶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震晕,羡慕嫉妒恨,觉得这样的小说才叫小说,由此迷恋先锋小说或者新小说,渴望写出主题深刻、细节精巧、语言独特的作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