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射灯的强光肆意在黑丛间蹦跃疾舞,毫不定点,况连忙促停被头带勒得涨坏的脑袋,头定灯定;伸手只见被五指活活撑开的白胶手套,像五条过熟的肥香肠。那片幼叶究竟在哪儿?迟不生早不生,入冬以来最寒的凌晨你才面世,恐怕上级又嚷着要给你注个记录。况心里愈骂,眼睛愈灵,别吵……“香肠”们缓缓拨开射光下的那束壮枝,果然藏着一片苦苦发红的嫩叶!谢天谢地,况立刻低头,好让射灯照照腰侧的工具袋。都说新购的这款发光药水红得沉,不好找,可我这种人的意见呀,好比百年树根吸收的水分,要传到至高无上的那层叶,非要花上巨大的力气不可。况的怨气随呼吸化成轻透的雾姿,从口绽开;白手套托着的初生叶,战战兢兢地瞄读另一只白手套的居心——况正要向叶打下纤维芯片。“咔”,幼叶穿孔了。当小孔愈合时,芯片自然悄悄生出,像胎记。
弄妥幼叶后,红褪了。况先后检查现场的探测器和中央的总指挥机,没有新信。这二十四小时轮班制荒唐得来仿佛还真有点作为,况一边扯脱那双黏缠的手套,一边对自己开玩笑。颈项和头颅被探射灯策骑得左酸右麻,额上那圆印该赶得及于天亮前消隐吧。搓搓额,伸伸腰,果然换班了。
“钉了一片新叶,十四路南段杂草的折曲度快到黄色级别的上限,还有……多穿点衣服,冻病了请假不容易。”况把工作记录本推到书桌中央,拍一下打呵欠老是不掩嘴的尤的右肩。
“辛苦你了,师兄!这儿交给我吧!”尤顺手把眼垢糊在记录本的封面,向况挺不直的宽背挥手。
吸入提神的寒气,况步出护林局辖下的第二百六十四号看守亭,行内俗称“荫亭”。他的四肢居然蠢蠢欲动,想来个晨操,奈何时辰总跟心情不配,通宵后当然先大睡一场。尤口中的“这儿”,于日光下是三条平行的横巷,微曲上山,邻旁盖了数间零落的平房,新旧分明,闲时野猫野狗几乎还比人车热闹。可不论地段,签下护林局四级林木监护专员的聘书,工作准离不开打芯片、数落叶、照色变、算风速、称泥土等。况自知不是植物学的材料,家族又跟农务无关,真弄不清三年前向局方报名的动机。
动机?找工作几乎是本能吧,反正动机还没猜透,对方已快人快语数列雇员合约的这项那项。动机?被选中便是应征者的动机。
三年于况而言,不过是年份的个位加一加一再加一。生活循环,植物也循环,可后者劳师动众得多:全城的公共地方种植的高矮壮嫩配有编号牌不说,连泥土也按品种注入监控药水,新叶发红,缺水发紫,落叶前夕发灰,开花时更会发声,“噗”!几乎吓坏鸟儿。每片叶每朵花必有芯片,保证生长数据实时发送至护林局。数据拿来干什么?况当值时不时随意问问枯叶,管他!反正局方偏爱收集,传媒又矢志追问,发点薪水我便给你做数据,不难!可怜功夫做得勤,叶枯花凋还是常事,冤枉!
严冬的日光稀有得来分外灵白,况把内外两层窗帘拉闭仍无补于事,可他早已适应于一片舒白下入睡,像天堂,只是楼下的车水马龙着实有点反差。被子盖过头会好些吗?不,还是听到哪里来的家伙敲响电话。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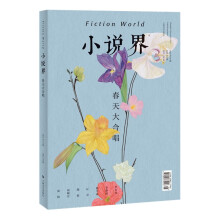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这不是一个甘于庸常的年轻人,她(陈苑珊)找到了一种“创世”的方法,即是以怪诞、变形、夸张的方式,将人们见怪不怪的世相,加以放大、显影,将凡人视而不见的流行疫症病毒曝光现形。
——蔡益怀(《香港作家》总编辑)
陈苑珊文字整体很像西西,充满一身的视点,新生般的世界。……我觉得(陈苑珊的)文字充满魔术,一种来自异域的陌生感。
——陶国璋(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