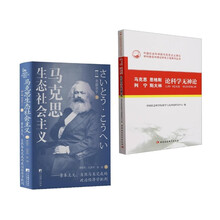琉璃厂气氛
乾隆时益都李南涧(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中写道:“……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抄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鲁迅先生一生不喜欢看京戏,那时应酬也不多,平日公余除抄书之外,一遇暇日便到琉璃厂游览,很像李南涧所说的那种情况。
琉璃厂后来习惯说在和平门外,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因为和平门是一九二四年左右才开的,南北新华街也是同时才展宽的。在鲁迅先生去琉璃厂买书、访帖的大部分时间里,由城里去琉璃厂,还是不出宣武门,就得出前门,中间全有城墙挡着,是过不去的。鲁迅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在宣武门里教育部上班,不论星期天或平日,去琉璃厂都是很方便的。走大路从菜市口经骡马市到虎坊桥,从梁家园斜穿过去,顺新华街往北不远就到厂桥,就是东西琉璃厂的中心了。如果走小路,从菜市口东边一点,进铁门穿小胡同到南柳巷,那就更没有多少路,便到了琉璃厂厂西门了。
琉璃厂以厂甸海王村公园为中心,往东是东琉璃厂,接一尺大街、杨梅竹斜街;往西是西琉璃厂,接南北柳巷。过去东西两头都有铁门,俗名厂东门、厂西门。整条琉璃厂街上,由鲁迅先生时期,一直到后来,除去西琉璃厂路南商务印书馆一所三层的西式楼房而外,其他都是中式的铺面房,而且大多都是平房,间或有所两层的楼房,那也有如凤毛麟角了。不过这些铺房都很精致,一般都是水磨砖的砖木建筑,门面油漆得很整齐。开间大多都是二间、三间,五间的便是大店了。只有昔时宝名斋书铺是最突出的,九开间门面,当时人称:“琉璃厂一条龙,九间门面是‘宝名’。”不过在鲁迅先生时期,宝名斋书铺早已关张,其他那些店铺,门面虽然不大,但后面进度一般都很深,而且都连着后面的院子,这样地方就很宽绰了。
琉璃厂各家店铺,大多都没有西式店铺的那种窗橱;也不像江南店铺的那种排门板,白天去掉门板,店面敞开,无门无窗。琉璃厂店铺的门面,都有门有窗,窗上装玻璃,有的还是老式窗,下面玻璃,上面糊纸。店门后来大多改为西式拉门,过去则都是对开木门,白天开门营业,门上挂帘子,冬天蓝布镶黑云头夹板棉门帘,夏天夹板大竹帘,从街上走过,透过擦得十分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店内的一些风光:古玩铺的红木多宝槅上的花瓶、鼎彝;书铺书架上一叠叠的蓝布套夹着白色签条的古书;书画铺挂的各种字画、立轴、对联;墨盒铺架上的亮晶晶的各式各样的墨盒子、镇纸、笔架……店名一般都是黑地金字的匾额,几开间门面的大店,在店名大匾的两旁,还对称地挂上两块小匾,如“藏珍”、“蕴玉”之类。柱子上都有红地黑字或黑地金字油漆得亮晶晶的抱柱对联。牌匾、对联都是当时名家书写的,翁同龢、朱益藩、宝熙、陆润庠等,应有尽有。这些对联都是嵌字格的,这里抄几副在下面,作为当日琉璃厂的一点资料吧。
宝气腾辉瞻典籍;
林花启秀灿文章。
宝林堂书铺
崇山峻岭琅嬛地;
文薮书田翰墨林。
崇文堂书铺
宝鼎芝房,嘉祥备至;
文场笔阵,典籍纷披。
宝文堂书画铺
万象峥嵘新眼界;
元龙品概古胸襟。
万元眼镜铺
这些对联,切铺名,切店铺内容,对仗一般都很工稳自然。尤其万元眼镜铺一副,用陈登的典故用得很好,很有点气概。
琉璃厂东西街,不管从东从西,慢慢走来,总是笼罩在一种文化、艺术的气氛中,这种气氛是琉璃厂所特有的,是从清代乾隆、嘉庆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直绵延到后来,其间将近二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
鲁迅先生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京,十二日就到琉璃厂游览,日记上记道
星期休息。……下午与季茀、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籑]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
其后,二十五日又去,二十六日、三十日又去。初到北京,风尘仆仆,除工作之外,朋友往来也很忙,却在不到一月之间,便去了四次琉璃厂,可见厂肆与先生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与当时所有学人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了。自此以后,十五年中,浏览古书,访求碑帖,收集信笺,时时徜徉于海王村畔、厂肆街前,那去的次数就更多。
先生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最后一次回北京,在京住了十六天,又去了三次琉璃厂,二十七日记道:
午后往师范大学讲演。往信远斋买蜜饯五种,共泉十一元五角。
先生这次往师大讲演,后来到信远斋买蜜饯及回家,是当时师大同学叫营业汽车接送的,这便是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去琉璃厂。在东琉璃厂进口不远路南,那小小的两间门面的信远斋,嵌着玻璃的绿油漆的老式窗棂,红油漆的小拉门,前檐悬着一块黑漆金字匾额,写的是馆阁体的“信远斋”三个字。在初冬下午的阳光斜照中,鲁迅先生提着几包桃脯、杏脯之类的蜜饯,在店主萧掌柜拉门送客,“您慢点儿走……回见……”声中走出来,坐上车,回到城里西四宫门口家中。这普普通通的一点情景,谁能想到这就是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告别自己多年来不知徜徉过多少趟的琉璃厂呢?真是“逝者如斯夫”,此情此景,应该早已和琉璃厂的气氛融合在一起了吧。
厂甸的书摊
厂甸期间,除去古玩摊而外,最多的就是书摊了。厂甸南北、新华街马路西侧人行道上,几乎全是书摊。海王村公园西门对面土地庙内,也都是书摊。书摊虽然不像珍宝摊、古玩摊那样讲究,但也可以分出若干等级来。大体是土地庙中、海王村公园左边的大书摊,都是一等的;马路西侧,人行道上的书摊,是二等的;离热闹区远的边沿地区的便是三等的了。大书摊也都是用木板搭成货台,临时营业。北京是几百年的文化古城,学者多、教授多、教员多、学生多,所以书摊边上簇拥的人也绝不比珠宝摊、古玩摊的人少,同样是拥来拥去。鲁迅先生甲寅(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记道:“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朱逷先、钱中季、沈君默。”二月八日记道:“……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从这些日记中,很可以窥见当时厂甸书摊上,是学人们常常见面的地方了。这种风气应该是流传很久了吧?过去常说王渔洋当年,人们不大容易找到他,只有在慈仁寺书摊上才能一瞻老诗人的风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燕台杂咏》中“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句下自注道:“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这故事传作艺林佳话,风气绵绵未绝,直到鲁迅先生他们在厂甸逛书摊时,也还是如此,也可见其悠久了。
厂甸的大书摊,除去本琉璃厂的一些书铺摆设而外,还有城里隆福寺街、宣武门里,以及东安市场和后来的西单商场等处的书铺、书摊,到期也到厂甸来设摊。尤其是隆福寺街的书铺,那时也有几十家,规模都不比琉璃厂的书铺小,其中如三槐堂、宝书堂、带经堂、聚珍堂、文奎堂等,都是很有名的老铺。这些店铺来摆摊,摆出来的书自是很可观的了。当然都是线装古书,其中不乏精刻善本。至于一般平装本、精装本的现代旧书,那都是在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各家书铺所设的摊子上出售了。除此而外,至于那些再次一等的,货色也就比较零散、残缺,这些书摊平时也都是在城里各小市或庙会上摆地摊,厂甸期间,也都集中到这里,希望多做点生意。这种摊子,也同古玩摊的地摊一样,货色残缺,生意清冷,当时习惯叫做“冷摊”。但是就是在这种冷摊上,却常常得到意外的收获;当时大书铺的店主、伙友也常常从冷摊上觅书。远的不必说,晚近文德堂主人韩左泉就从西小市摊上买到过绍兴刊本《后山诗注》,经傅增湘、赵斐云等专家鉴定后,藏之居为奇货。鲁迅先生一九二三年旧历正月初六日记道:“又在小摊上得《明僮欱录》一本,价一角。”正是从这种冷摊上买到的。先生特别记用“小摊”二字,多少表现出一种意外收获的兴趣。那时人们习惯叫做“淘旧书”,意思是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似乎像淘金沙一样,要花工夫在许许多多的沙中淘得一点,所谓“凡所难求皆绝好”,恐怕其乐趣也就在于此吧。
鲁迅先生在游厂甸的日记中,常常记着书价昂贵的话,如甲寅(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记道:
……因赴留黎厂,盘桓于火神庙及土地祠书摊间,价贵无一可买。遂又览十余书店,得影北宋本《二李唱和集》一册,一元;陈氏重刻《越中三不朽图赞》一册,五角,又别买一册,拟作副本,或以遗人;《百孝图》二册,一元;《平津馆丛书》(重刻本)四十八册,十四元。
又如乙卯(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日记道:
下午往留黎厂及火神庙,书籍价昂甚不可买,循览而出。别看书肆,买《说文句读》一部十四册,价四元。
这些都是很实在的情况。过去厂甸正月竹枝词有一首说:“火神庙接吕祖祠,购买新书归去迟。价比坊中平日贵,两人笑向说便宜。”就是说摊上的书价钱比店铺里的还要贵,而买的人却说“便宜”。这是什么道理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掌握了商业心理。原因是城中各书铺,到厂甸设摊临时营业,厂甸庙会人多,大家都认为能买到便宜货,书铺便利用这种心理,摊上的书普遍加码出售,而一般赶热闹的人便都认为便宜了。但遇到经常买书、熟悉行市的老客人,便自然看出摊上的书实际价钱很贵,反不如到书铺里面去买,一般都是熟人,倒还要公道实惠些。所以鲁迅先生几次都是浏览了书摊之后,又到书铺中去买一些自己看中的书。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书摊上虽然价钱贵些,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游人立在摊前,取阅方便,任何人都可以立在摊前翻阅,拿起一本来,看上很长时间,他也不会见怪你,不买也没有关系。所以即使买不成书,书摊前面的人还是川流不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你想看而没有看到过的书,看到你从未听到或想到的书。在逛书摊时也使人增长了不少知识,从某种程度讲,比你去图书馆查书卡借书看,要方便、实惠的多,只可惜这种书摊现在已经成为《广陵散》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