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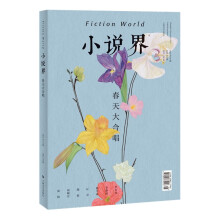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格林克兰茨
这座城市里居住着两类人,唯利是图者和他们的牺牲品。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若想在这儿生存,只能采取一种痛苦的、往往极为险恶乃至致命的方式。这一方式阻碍着每一种生灵,使其日益迷惘并陷于毁灭的境地。一方面,极端的天气条件不断伤害着这里的居民,消磨其精力,随时会引发疾病。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萨尔茨堡的建筑对人的状态也产生着日益恶劣的影响。无论这些可怜人是否已意识到,但从医学角度看,前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气候是绝对有害的,它压抑着大脑、身体以及完全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天性。这样的气候以惊人而放肆的方式一再造就出令人困惑、令人疲惫、令人病态、令人羞耻、天生卑鄙的居民,一再造就出这样一些萨尔茨堡人,他们或土生土长或迁居而来,与三十年前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我一样,居住在被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因与生俱来的喜爱而爱过,但也因种种经历而憎恶过的冰冷潮湿的围墙之中,放任自己狭隘的顽固、荒唐和愚蠢,从事着残酷的工作,陷入忧郁,最终成为所有可信或不可信的医生及殡葬公司取之不竭的收入来源。这位在这座城市里顺从其监护人的愿望,但却违背自身意志成长起来的人,由于甘愿为了这座城市付出情感和理智,一方面从幼年起就受制于世人对这座城市的名誉的公开监督,如同被锁进了一台既生产金钱又反对金钱的有违常理的美化及谎言机器,而另一方面,他在童年及青少年时期资金匮乏、孤立无援,无人荫护,仿佛被关入了一座弥漫着不安和恐惧的城堡。
这个注定要生活在这座城市,要在这里形成自己的性格和思想的人,他以既非过于粗俗,亦非过于轻率的方式叙述了自己关于这座城市以及城中生存环境的回忆。这些回忆更多是悲伤的,对他最初和早期的发展更多产生了极其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可怕的回忆对他的一生也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他拥有的唯有这样的回忆。除却诽谤、谎言和虚伪,他在撰写这段回忆时不得不对自己说,在他一生中,特别是在他在这座城市里生存和受训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在那段为期二十年的绝望期和成熟期,他的精神和情感受到了严重伤害和虐待。这座浸润其天性并主宰其理智的城市,不断直接或间接地惩罚和处置他未曾犯下的过失和罪行,打击着他的各种敏感和善感,而对他的创造性没有任何促进。这一求学阶段无疑是他经历过的最恐怖的时期。其间,他不得不为他的余生付出了巨大代价,或许也是最昂贵的代价。这里记录的是他这一求学时期以及他在此期间的感受。这座城市配不上他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预先存在的喜欢和爱心。迄今为止,在任何时期和任何情况下,它都在拒绝和排斥他,并对毫不设防的他进行攻击。假如我没能在那一瞬间,在令人神经紧张、极有可能造成精神伤害、性命攸关的时刻告别这座城市,告别这座始终在伤害、蛊惑并最终摧毁具有创造性的人的城市,这座由于我的父母而同时成为我的母亲之城和父亲之城的城市,我就会与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富有创造性的人一样,与我的许多亲朋好友一样,亲身验证这座城市独有的考验。我也会和许多身处其间的人一样突然结束自己的性命,又或许会在它的围墙中,在那令人窒息的、令人完全窒息和泯灭人性的氛围中慢慢地、痛苦地走向毁灭,如同许多身处其间的人慢慢地、痛苦地走向毁灭一样。
(著名的)自然风光和(著名的)建筑形成了我的母亲之城和父亲之城独有的特色和绝对的特征,我常常能够看出这一点,也喜欢这一点。但是在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建筑中生存着年复一年盲目增多的低能居民,他们、他们无耻的法律以及他们对其法律更为无耻的诠释总是将我对这一自然(风景)奇观和建筑艺术的认知和热爱消灭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之中。我个人的生存方式总是无力抗衡这个城市独有的小市民逻辑。这里的一切都与创造性相悖,而且也日益强烈地主张着其对立面。虚伪是它的基础,思想匮乏是它最大的嗜好。想象力一旦显现,顷刻即被消灭。萨尔茨堡是一个阴险的门面,世界不断地在它上面描绘着自己的谎言。门面之后,富有创造性的事物(或人)必然枯萎、衰败和灭亡。我的故乡实际上是一个不治之症,它的居民在这一疾病中诞生并感染上这一疾病。如若不能在关键时刻逃离,他们就会在所有这些恐怖情况下不是直接或间接地、或早或晚地突然自尽,就是在这块从根本上泯灭人性的,融汇着建筑风格、大主教、愚昧、纳粹和天主教气息的死亡之地直接或间接地、缓慢而痛苦地走向毁灭。对于了解它及其居民的人而言,这座城市尽管外表光鲜,但外表之下却是一座埋葬了一切想象和期许、真正阴森恐怖的坟墓。这座城市无处不在展现着美丽和辉煌,而且由于所谓的戏剧节,它也长年享有全部高雅艺术的美誉。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试图在这里如鱼得水,寻觅公正,可是不久他们就会发现,这里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充斥着疾病和卑鄙的死亡博物馆,这里存在着一切可以想象和不可想象的阻力,它们肆无忌惮地摧毁、深入骨髓地侵害他们的精力、智慧和禀赋。很快地,这座城市对他来说不再意味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建筑艺术,而无异于一座由无耻卑鄙之徒组合成的无法穿越的丛林。当他步行在城中的胡同时,他不再如同行走于音乐之中,而只是感受到对当地道德沦丧的居民的厌恶。以他当时的年龄,对于他这个突然在这里被骗取了一切的人而言,这座城市无法让他冷静,而是令他恐惧。这座城市也为一切,也包括震撼,提供了致命的论据。我当时的感受(感觉)以及现在的想法都在说,那个十三岁的男孩突然遭遇了一种严酷的现实:在位于施冉伦胡同的寄宿学校里,他和三十四个同龄人挤在一间肮脏的、散发着由斑驳潮湿的墙面、破旧的床单以及脏兮兮的年轻寄宿学生发出的混合臭味的寝室里,几个星期都难以入睡。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突然被迫睡在这个又脏又臭的大寝室里。他难以理解受教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一定是一种出卖。夜里,他观察着这个公共教育机构大寝室里的种种堕落,观察着这个教育机构本身以及不断住进这里的人。寄宿生都来自农村,和他一样都是因为顺从了父母的意愿而被送入国家的规训机构。夜里,他不得不发现,那些筋疲力尽的人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入睡,而他自己,尽管更加筋疲力尽而且内心始终饱受煎熬,却一刻都无法入睡。夜晚在绝望和恐惧中蔓延。他听到、看到,以及在持续的恐惧中感受到的,永远只能滋生新的绝望。
对于这位新生而言,寄宿学校是一座为了抑制他和他的整个存在而精心设计的、无耻地摧残他思想的牢笼。(格林克兰茨)校长和他的帮手们(看守)掌管着这里的所有人和一切事物。学生必须绝对服从,亦是绝对屈服。弱者屈从于强者(格林克兰茨和他的帮手),只能保持沉默,安于黑暗。在他看来,牢笼般的寄宿学校意味着日益加重的惩罚,其尽头是困境与绝望。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一直以为爱着他的人会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把他送进这个国家监狱。
在最初的几天里,充斥在他脑海的自然是自杀念头。在他看来,为了不再继续生活或生存而摧毁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向窗外纵身一跃或选择在底层的鞋屋悬梁自尽来为这一突如其来、孤立无援的状态画上句号,这似乎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法。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格林克兰茨把鞋屋分给他练琴。在鞋屋里练习小提琴时,他总是想到自杀。在鞋屋上吊最容易,找到一根粗绳也毫不困难。第二天他就用裤子的背带试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并接着练琴。之后,每当他走进鞋屋就产生了自杀的想法。鞋屋里腐旧的木质鞋架上满满堆放着几百双被汗水浸湿的学生鞋,只在紧贴天花板的墙角开了一扇小窗,飘进来的也只有厨房排出的污浊空气。在那里他可以与自己为伍,独自沉浸在自杀的冥想之中。自杀的想法总是随着琴声而开始。鞋屋无疑是整个寄宿学校里最可怕的一个房间,走进鞋屋就是逃离到自我之中。练琴只是借口,他在鞋屋里大声地拉琴,声音大到连他自己也不断担心鞋屋会在练琴过程中随时爆炸。
……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在萨尔茨堡州,每年都有两千人试图终结自己的生命,其中十分之一Z终死亡。在与匈牙利和瑞典同为自杀率Z高地区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因此保持着奥地利的全国纪录。
——1975年5月6日《萨尔茨堡新闻报》